|
罗家五世显
作者:罗 宏http://www.luos.org
鼓磉洲罗氏五世而显。
此时罗氏迁湘约百年,罗氏三代之后以源佐的四个儿子志聪、志明、志安、志亮分堂,即新屋堂、湖田堂、社山堂、蕨山堂,四代又分10房,五代达53房,至六代又分支,排除无后之房为42房。亦即,百年之后的罗氏已是四堂42房的大家族。五世祖罗瑶便是标志罗家崛起和显望的符号人物。他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罗家成为湖湘世家的开篇,也储存着罗家显望的奥秘。
罗瑶,字宗玉,生于明天顺五年(1461),父必高,祖志亮,曾祖源佐,高祖就是迁湘始祖罗应隆。族谱记载,罗瑶之父必高“生而伟异,丕振家声,慷慨仗义,好善乐施”。可见罗瑶之家在父辈就开始发迹,至罗瑶更是发扬光大,成为湘中首富。族谱如是说:“公富甲中湘,克承父志,推仁慕义,阖邑赖焉。”罗瑶的亲家,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凤阳知府邓巍作为同时代的见证人写罗瑶家“耕牛过千头,童婢五百人”,仅这两个数据,就够惊人。方志和民间传说,对于罗瑶的富有,均一致认同。如说,罗瑶田产有四个九,即万亩良田仅差一亩,还说,湘潭城的产业,一半属于罗瑶。故民间有“罗百万”“瑶半城”之说。显然,财富是支撑罗家显望的基础性条件。
湘潭,乃湖湘最为富庶之地,它毗邻长沙府郡,从南朝开始建县,一度升为州郡,悠悠1500余年,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扼守湘江水路枢纽,成为商业繁荣的大码头。元明之交战乱,湘潭是重灾区,因为人口锐减和原有经济秩序的破坏,导致经济实力的下降,但既有的历史和地理区位基础,令其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并非不可想象。事实也证明,经历明初的阵痛,湘潭很快恢复了经济生机,其中原因又与江西移民大量进入湘潭密切相关。《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有这样一段阐述:
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文化世家属湘潭地区的最多,有11家;其次是长沙地区,有9家。两者相加,接近总数之半。而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则相对比较分散。湖南文化世家的大量涌现主要是清代。清初湖南单独建省,长沙成为全省政治中心。但清代前期湘潭的经济发展超过了长沙,故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湖南的文化中心一直位于湘潭……清代征市租,筹捐输,每岁输过万金按比例可以增加学额一员,湘潭“常一岁例额七十”,如此巨额的数量,其他任何一地都望尘莫及……因此湘潭在清前期进士人数在全省独占鳌头,远出于长沙、善化。
以上资料是从文化世家的角度论证湘潭的优越性,意味着湘潭也是英杰密集的高地。再仔细辨识这些世家的来路,都是移民家族,尤以江西移民为最。于是,江西移民群体推动湘潭的战后复兴便成为必然。明代以前,江西的农业生产就优于湖南,移民进入带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此外,江西商业发达程度更优于湖南,赣商属于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加之江西移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于湘人,借助历史形成的优越区位基础,明代湘潭便成为农业发达、商贸繁荣、富甲三湘的“小南京”“金湘潭”。明代以湘潭为中心的湘中平原是中国的粮仓,湘潭码头是辐射全国的米市码头,其商贸繁华超过长沙,成为湖南首屈一指的商贸中心。明代进士、礼部尚书,也是湘潭人的李腾芳充满傲气地问:“试问湖南诸邑,其为水陆之会,上下散聚之门户,谁如湘潭?大盗之作,必有小盗为耳目,故四方作奸犯科之人,多以手作、工技、乞食侨居者,虽未必皆盗,而盗在焉。然是人耳,非百货辐辏之地不居,而试问湖南诸邑,其钱币所集,流移所聚者,谁如湘潭?”
可以认定,明清湘潭之富,得益于湘潭优越的区位条件,也得益于战乱引起的江西移民进入。罗瑶作为抢滩登陆湘潭较早的移民之后,在湘潭崛起成为新富,实在有赖于这种时势的眷顾。
诚然,罗瑶能在英雄逐鹿的湘潭脱颖而出,富甲湘潭乃至富甲湘中,除了大势眷顾,必有过人魅力,可惜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其致富之术。家谱资料由于避讳扬善的本能,具有相当的遮蔽性,也使人对罗瑶的富有怀抱道德警觉。的确,财富的积累往往伴随着拼搏的刀光剑影乃至血腥,难以通过道德审判,比如罗瑶的亲家周环,也是江西移民湘潭后发达的巨富,其发家之初,就有毒杀胡椒客的传闻,后来王闿运撰写《湘潭志》记载了此事,遭到周家指控,只好删除。那么,罗瑶的富有,是否也有类似尴尬?倘若平心静气,当然不能排除罗瑶奋斗史中的污垢,然而又要警惕另一种偏执,即富人即恶人、穷人即圣人的荒谬判断。人类的历史进程毕竟是不断摆脱贫穷而求富的历程,衣食足而礼义兴是更有说服力的历史逻辑。史料记载,罗瑶和周环显富后均有回馈社会的义举,周环在嘉靖年间的湖南天灾中曾捐谷一万两千石济民,还捐学田数百亩支教,这都不能简单理解为收买人心的阴谋,而应更多肯定其中对社会的建设性。
时值明朝中叶,严嵩专国,吏治败坏,巧立名目的税赋日益加重,而湖湘大地又连年遭遇水旱天灾,“大湖以南,疲困极矣”。史料留下如是记载:“公独慨然以一邑为己任……出谷千石以实之,赖以活者万计。”至于接济族亲,更不计其数。如此义举,自然奠定了罗瑶的社会名望,湘潭地方要事均会征求他的意见,并往往委以主持之任。如湘潭学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罗瑶不仅建议迁址重建,还独资修复。此外通往省城、扼守京广官道的暮云桥,也是罗瑶独资兴建。种种义举,均载于邑志。湘潭民间流传许多罗瑶乐善好施的逸事,下面这个故事,便流传了600年。
一次,湘潭议修县城,县太爷召集全县豪绅捐款。众豪绅到齐后,县太爷还不开口,只问:瑶公到了吗?这时,一个土气的乡下老农民走进来,县太爷连忙起身把老人推上首席,向大家介绍,这是马家河的罗瑶公。于是才宣布议事,众豪绅很不服气,也无可奈何。县太爷说明了修城募捐的意图后,摊开捐簿要各位豪绅认捐。大家都你推我让,不想当出头鸟,就把捐簿推到罗瑶面前,要他先认,也想探探这个乡下土财主的虚实。罗瑶却说,还是诸公先认,剩下的我想办法。大家一听,这老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乡下人,有点傻。于是都写下很小的数额,一是吝啬,二是要看这乡下老头怎么收场。最后到罗瑶认捐了,县太爷一看前面认捐数额,倒抽凉气,预算的一半还不到!哪知罗瑶眼皮都不抬道:剩下的我全包了!大家一听,目瞪口呆。县太爷顿时大喜,说:那好,湘潭城的围墙,一半城墙砖都刻上瑶公的名字!从此,罗瑶有了“瑶半城”的称号。
这个故事据株洲民间故事资料整理而成,故事里的罗瑶成了一个土气憨萌的乡下老财主,并不立体全面,不过,倒是写出了一种乡下牛人对城里牛人的不屑,烙印着那个时代的乡村自信与自得。财大气粗,人之常情,也是民间经验的归结。而在农耕时代,乡村财主不仅仅意味着锦衣玉食,还意味着对社会话语权的掌控,比如大财主罗瑶便成为参与甚至主宰地方事务的乡绅贤达。宗法社会的中国,官权从来止于知县,县下的广大乡村则是财主乡绅承包的天下,官权与绅权(族权)配合默契,方能治理中国。故而有乡村中国、乡绅中国之说。这个县太爷向乡绅募捐修县城的故事,不经意间也透露了传统中国的治理奥秘。富豪罗瑶乐善好施的行径背后,显现出宗法制度的管理设计,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其乡绅的社会义务,既然在乡村享有族权,便要同时尽一份奉献义务。在履行乡绅义务的过程中,又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这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罗瑶,清代进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山西学政蔡扬宗撰有墓表,这也是一篇介绍罗瑶最全面的史料,其中有如是描述:
公讳瑶,宗玉其字也。生而伟异,修眉广颡,茂外朴中,读书务经世之学,论天下事,多奇中……遇事风发雷动,讽贪官、成廉吏、劝士人、收弃妇,至今里老犹有能道其轶事者。天性孝友,处门内有古人风。父没,卜吉于河北牛形山,会葬者数千人,七郡豪贤皆至,率子弟庐墓累年。当是时,子若孙登仕籍者六人,游庠序、贡成均者十余人。而公家政严,一门数百口皆循循矩矩,时人比之张郑。分巡佥事王公乔龄具其事以闻,敕建崇义坊以旌之。先是,郡有大僚欲以人材荐公于朝,辞不就。时论益高之。没年八十有一。以孙轸阶赠承德郎。至明末,公之后裔遭遇时艰,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著,或以文章、隐德称,故两朝鼎革之际,邑之缙绅阀阅,大半凋零,而鼓磉洲罗氏岿然无恙。国朝承平百有余年,人文之盛,邑之巨族,亦未有能过之者。天之报施善人,果何如哉!
这篇墓表是蔡扬宗受罗氏十三世传人也是罗瑶八代孙罗升所托而撰。这罗升也是一代才子,与湘潭张贡五、胡苍崖等并称“湘江六子”,曾任石门教谕,与蔡扬宗不仅是同窗,还是亲家。因此蔡文多有溢美自在情理之中,不过也正因为和罗家的亲密关系,蔡氏对罗瑶及其家族也有更深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罗瑶是读过书的,读得还很透,他读书主张经世致用,而且关心时事,发表意见往往奇准,说明罗瑶是个务实并胸怀见识的人;第二,由于罗瑶见识超群,有大官要推荐罗瑶入朝为官,罗瑶拒绝了,显示了清高孤傲之气,与权力保持着距离;第三,罗瑶急公好义,不媚权贵,敢担当,性刚烈;第四,罗瑶崇文教,讲节操,很有人格威信。这些表彰可能有夸张,但从罗瑶受到的社会尊敬以及史料看,大体还是可信的。其实,这也可视为对鼓磉洲罗氏家族文化性格的概括。蔡扬宗墓表暗示,罗瑶的人格榜样被家族后人发扬光大,由于这种秉承,罗瑶后人历经明末乱世,“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著,或以文章、隐德称,故两朝鼎革之际,邑之缙绅阀阅,大半凋零,而鼓磉洲罗氏岿然无恙”,成为湖湘巨族。自罗瑶之后,家族文武英杰迭出,绵延500余年,在湖湘世家中,鼓磉洲罗氏并不是出产文豪大吏最多的,却是保持世家气象最悠久的少数世家之一。
罗瑶发家成为大财主,并不能必然地成就其家族后来成为享誉湖湘的文化世家,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很值得一说。
罗瑶乐善好施,尤其对文教十分热心,他不仅出资办学,还对贫苦学子解囊相助,有名姓的受惠者达数十人。于是民间又流传着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某夏天的中午,罗瑶躺在堂屋午睡,悠悠入梦。梦中一老者走来对他说,请你记住鱼上树、马骑人的时刻,若有人与你见面,千万不可错过。罗瑶醒来,琢磨梦境,百思不解。他踱步走出门外,见一人在门前树下歇息,将一条鱼挂在树上,另一人却背着一只木马走来。罗瑶一愣,这不就是鱼上树、马骑人吗?就在这时,一个小乞丐打着莲花落乞讨走来。罗瑶转身看,这小乞丐生得眉目清秀,口齿伶俐,便询问起来,得知他叫张治,茶陵人,因家贫而行乞。问答间罗瑶断定,这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加上梦中的神示,罗瑶便将张治收为义子,并延师教读。那小张治果然聪明勤奋,学业日进,罗瑶更加喜欢,又把收养的义女嫁给了张治。后来张治考科举,竟高中会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人称张阁老。张治显贵后,对罗瑶终身感恩,对罗瑶的后代也关怀备至,成为罗瑶儿子们的老师,并精心栽培他们。罗瑶死后,张治买下鼓磉洲岛,厚葬恩公,亲笔题写墓碑,还促成嘉靖皇帝敕建崇义坊以旌。鼓磉洲罗氏因此大显一方。
这个民间故事亦见于株洲文史资料,除了梦示,基本上有信史支撑。有趣的是,在张治的家乡茶陵的文史资料中,也记载着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这样说的:
张治小时候家贫,虽然被茶陵知州看中,补了州学生员名额,却读不起书。母亲就带着十来岁的儿子出外乞讨,希望遇到好心人资助,于是就来到湘潭巨富罗百万门下。一番问答,罗百万看中了张治,就说,我的儿子和你年纪相仿,就是读书不用心,你来当陪读吧。张治就成了罗少爷的书童,跟着少爷读书,果然学了不少学问。后来,私塾先生觉得张治的学问已不在自己之下了,就辞去了教职,并对罗百万说,茶陵是个出才子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张治将来必有大出息,他现在的学问教你的公子绰绰有余!从此,张治就成了罗少爷的老师。后来,罗少爷果然中了秀才,而张治则高中会元,成为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考中进士后,张治特意要报子先到罗家报喜,然后才回茶陵家中报喜。他终身不忘罗百万大恩。
的确,张治对罗瑶终生感恩。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瑶公去世,享年81岁,葬鼓磉洲岛,此洲即为张治专为恩公买下的官地。王阳明高足,时任湖南地方主官的王乔龄对罗瑶十分敬重,特上奏朝廷以表彰罗瑶,嘉靖皇帝准奏,敕建崇义坊以旌之。张治亲题墓碑,一时间传为湖湘盛事。规制宏丽的罗瑶墓一直保存至今,成为罗瑶故里(现为株洲)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株洲的一张文化名片。
罗瑶和大学士张治的缘分,是罗氏五世而显的重要契机。因此,了解一下张治对我们揭示罗家的显望奥秘至关重要。
张治(1488—1550),字文邦,号龙湖。祖籍江西,大约明初移民湖南,我们只知道其父叫伯诚,其母谭氏,兄弟姐妹均不详。有学者研究张治家世,说张治先祖跟随文天祥抗元兵败,惨遭灭族之灾,族人幸存者四处逃亡,张治父祖先人就是其中之一,辗转流落至荒僻的茶陵,以农为务,族脉一直没有起色,至其父辈更沦入贫寒境地,父为长工,母亲以纺织补贴家用,但依然难以为继,以至于母亲带着儿子乞讨。也就是在一次乞讨中,母子俩遭遇了湘中富豪罗瑶,得到资助,改变了命运。不过张治天资聪颖,也是不可忽略的。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给张治写的传记中说:“公生,神颖英拔,机撄慧动不可制,数岁,挥墨成巨字,稍长,偶词属对,应声谐捷,多非人思构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径白督学官,补充校弟子员,学官授以业,所摭经训微指,迎意辄解,旁及诸史百氏,靡不贯穿。及鄞张文定督学试之,见其文,愕曰:‘兹非刘、李匹亚耶?’盖指茶先辈坦斋、西涯二先生云。”
由于结识了富豪罗瑶,张治入罗家塾馆当了书童,后来又成为罗家少爷的小先生,家境大为改善,自己的学业亦蒸蒸日上。民间故事还说,罗瑶还把一位养女嫁给了他。28岁那年,张治中举,同年其父病故,可谓悲喜交加。不难想见,罗家肯定又施以援手,激励张治迈过这道人生之坎,向仕进的高处登攀。五年后的正德十五年(1520),33岁的张治终于高中会元,一时间声震湖湘士林,光耀乡里门楣。据说该年茶陵的龙化湖突然干涸龟裂,应了传言“龙湖干,榜元出”,张治喜不自禁,便给自己取号龙湖,此后他以“龙湖先生”名世。
张治高中会元的次年,又在殿试中以二甲第60名进士及第。就在这年,沉溺于风花雪月、才31岁的明武宗驾崩,意味着一个荒淫的旧朝过去,也意味着朝政会有新格局。这对张治而言应该是个好开始,然而后来的故事表明,他与新到来的嘉靖朝格格不入。
嘉靖一朝,宫廷斗争极其复杂尖锐。开朝就是大礼仪之争。由于明武宗无后,首辅大臣杨廷和及一帮前朝旧臣议定迎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新帝,即明世宗,却不许世宗尊亲生父母为皇考妣,而逼他尊伯父明孝宗为皇考,引来世宗抗拒,君臣间爆发了大礼仪之争。在一大帮前朝旧臣的围攻下,世宗一度陷入孤立之境。这时与张治同榜的新科进士张璁敏锐地抓住机遇,冒死一搏,联合刑部主事桂萼力挺世宗,与杨廷和等群臣展开了激烈争辩,几经起伏,皇权终于以左顺门血案(即世宗派锦衣卫捕杀杨派群臣)而取得胜利。大礼仪之争表面看是孝德规范之争,实际是皇权与臣权的博弈。张、桂也因拥戴皇权而获升迁,击败了杨廷和一派,把持了朝政,成为新一代阁老权臣。
显然,这对张治也是一个迅速上位的机遇,事实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宫斗中,他也站在张璁阵营中,却没有像张璁那样获得丰厚回报。表面原因是他的态度不够鲜明激烈,没有像张璁那样赤膊上阵,深层原因则是其性格的拘谨持重,换言之,他缺乏张璁那样的政客与赌徒禀赋,其人生的沉浮均可归结于此。在雷礼的《张治传》中,有张治不满张璁、桂萼弄权用事的表述,甚至称张治与张璁不和,归乡避祸达六年以上,因而影响后来的作为。许多学者也沿袭此说,其实这样的说法是误解。明世宗在左顺门血案取得胜利后,立即组织张璁等人撰修《明伦大典》,以求在礼法上巩固礼仪派的意识形态,张治便是张璁班子的撰修官之一,而且修完《明伦大典》后,张治受到嘉奖,得升左春坊左赞善(六品),可谓佐证。之后才出现嘉靖七年(1528)张治母病,他告假回湘侍奉母亲之事。嘉靖十三年(1534),张治再回朝廷,张璁已经下台。清代人陈田所编《明诗纪事》中收录了张治的十首诗,陈田按语道:“文毅当议大礼时,附和张、桂,与编修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俱与纂修《明伦大典》之列。未满考,擢赞善。《龙湖集》中颂罗峰阁老诗,备极推崇。厥后廷推阁臣,世宗持之十日,以南吏部尚书召入,殆犹忆议大礼功耶?”查《龙湖集》,果然可见张治多篇颂扬张璁(即罗峰)的诗文,证明陈田的说法是靠谱的。
对于张璁,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多有贬笔,斥之为小人。但正史,包括现代史学界的总体评价还是肯定为主,认为他是嘉靖初年的能臣和改革家,对于嘉靖中兴建有殊勋。对张璁的负面评价主要是专横弄权,得罪朝臣较多,一直受到攻击弹劾,加之他执掌朝政不过十来年,后来臣子由于派系原因,都忌讳和他有联系。其实嘉靖朝宫斗复杂而激烈,拉帮结派是官场的风气,缺乏帮派归属,缺乏霸气权谋还真难以在朝廷混下去,张之后的夏言、徐阶、严嵩等阁臣都是宫斗高手和帮派首领,相比之下,张璁的口碑还不算太坏。张治和张璁又是同年关系,交往密切并没有什么值得忌讳,倒是写《张治传》的雷礼可能因为帮派之见,有点想当然。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可能是张璁后来失势,张治夹在帮派缝隙中的自保说辞。这就涉及张治尴尬的仕途处境了。张治不是一个政治强人,在以心计权谋和厚黑手段为支撑的明代政治博弈中,其政绩是不显赫的。原因有多方面。他出身贫寒,身世坎坷,少年多受歧视,这对于他的斗争锋芒多少有压抑作用。他为人比较内敛沉稳,虽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却也不锋芒毕露,攻击性和冒险性都欠缺,甚至有点老好人意味,后来严嵩推荐他为次辅大臣,大概也看中他这个性格特点——好操控。此外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中进士后两次告假回湘侍奉母亲,按雷礼说时间有十三年之久(至少也有七年),甚至想放弃仕途,这无疑使他疏离朝政和官场的钩心斗角,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场逐鹿的局外人。严嵩也因为他没有帮派归属,身份超然,拉他为拍档。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洁身自好,不善也不屑于拉帮结派,因此也不能得到世宗真正赏识,其实嘉靖朝一幕幕宫斗大戏,可说都由世宗导演,从杨廷和开始,世宗就和群臣形成博弈态势,甚至二十年不上朝,拉开与朝臣的距离,却暗中制造群臣的派别纠纷,拉一派打一派,从中渔利,以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人说沉溺于求仙问道的明世宗是驾驭群臣的一流高手,并无夸张。张治显然对此无法适应,必然不为世宗真正重用。雷礼的传记中对他不吝美辞,但这些美德都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理解,并不能落实到“兼济天下”的作为上。故雷礼不无遗憾地写道:“博闻强识,性亢爽有气节,言论侃侃,临事不阿,是时,上崇尚焚修,辅臣悉供玄撰,殊不自得,遂郁郁成疾。及卒,上颇不悦,诏加以中谥。隆庆改元,乃更谥‘文毅’。”这段文字提及世宗沉溺道教,好青词(祭祀仙道的颂文),大臣们纷纷撰写青词邀宠,而张治独不为,但也不抗辩,不软不硬,使得皇帝不悦,却也不好责问。这大概也是张治的生存之道,既有节操的坚守,也有精明的自保。皇帝不会喜欢这样的臣子,他死后只得一个中等规格的谥号“文隐”便不奇怪(到了隆庆帝改元才纠正过来,改谥“文毅”)。张治母亲也只得了一个相当于三品衔的“淑人”封诰。总之,张治尽管贵为次辅,政绩却很不相称,其官宦生涯始终在帝王和权臣之间游荡,两头不靠,以道德论,可谓君子,以功业论,未免平庸。
要说张治在明代完全没有作为也不对。他最大的勋业是发现、提携了一批英杰人才。张治分别于嘉靖十三年(1534)、十四年(1535)、十七年(1538)、十九年(1540)、二十六年(1547)、二十九年(1550)主持南京或全国的科举考试,不难想象张治门下俊彦辈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有归有光、薛应旂、杨继盛、张居正、王世贞、徐学谟、李春芳、殷正茂等。
归有光是明代大文豪,唐宋派首领,散文大家,人称明代的欧阳修。嘉靖十九年(1540),他赴南京乡试,主考官正是张治。张治对归有光的考试文章赞不绝口,称其为贾谊、董仲舒再世,本想拔第一名,但考虑到考生的籍贯平衡,置第二。更重要的是张治对归有光以国士礼遇,使归有光声名大震。事过境迁,归有光还念念不忘当时的风光:
庚子之岁,举于南都,而所试之文,乃得达于左右,顾称赏之不置,时有获侍而与闻之者,辄相告以为幸矣。予之见知于当世之钜公长者如此。自后数试于礼部,遇明公之亲知,未尝不传道其语以为宠。(归有光《上徐阁老书》,《震川先生集》)
归有光说的“钜公长者”,就是张治,他把张治看作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张治也殷殷期盼归有光早日中进士,哪知归有光屡试不中,张治惋惜之余,甚至想动用权力举荐归有光进入仕途,可心高气傲的归有光婉拒了。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近60岁的归有光才中进士,此时张治已故去15年了,真让人感慨系之。必须承认,张治门生中,归有光、王世贞、薛应旂以文学名天下,杨继盛以忠烈名天下,还有登上尚书首辅高位的名臣张居正、徐学谟、殷正茂、李春芳等,均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桃李风光,要论青史留名,他这些学生的名气显然要大大超过老师,这又应了韩愈的说法: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培育了众多英才,应是张治的人生骄傲,遗憾的是,他的弟子均显耀于他身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治最后一次主持会试,命题即为“权臣不可有,重臣不可无”,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育才理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在这年十月,他患病去世,享年62岁。
了解了张治一生,回头再说他对罗家的感恩。
张治祖上也是江西移民,在茶陵,家族算是小姓。据《茶陵县志》,该乡有五大姓:谭、陈、刘、彭、龙。张姓是不到500人的小姓。张治28岁丧父,清代彭思眷编辑的《张龙湖先生文集》说“先生幼孤窘崎岖,负米之余抱守六籍”,可以推测其家脉是不兴旺的。他去世后,整理其遗著,初步编成《张龙湖先生文集》的是其女婿彭治中,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儿子,至清代编定《张龙湖先生文集》的彭思眷是彭治中的曾侄孙,亦即清代大学士彭维新的父亲。也就是说,张治是依靠女婿彭家的不懈努力,才留下了传世文集。这亦表明,张治男系后人凋零。在旧时代,这是很令人伤痛的事。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么张治对罗家的情感寄托就更好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罗家当作亲人来对待的。还有,张治在严嵩的威压下,并不得志,其人生是比较孤独和压抑的。诸此种种,都使得他内心情怀在很大程度上都接系于和罗家的交往。尽管他政治上难有大作为,但动用手中有限的权力庇护提携罗家子弟,还是不成问题的。
罗家族谱显示,罗瑶长子罗大钦有“明经”的功名,是罗家第一个有功名的。明代的明经是经有权力资望者推荐而入国子监就读的士子,可以绕过严苛的科举考试,直接授官,此后罗大钦之子罗栋、罗枬,大钦三弟罗大宪的三个儿子,都拜张治为师,并都得到张提携,走出了封闭的湖湘,进入了仕途。如,罗栋于成均肆业,授广东市舶提举,是管理广东对外贸易的从五品官职。罗枬也以明经出身,选授山西大同府经历,亦为六品官。还有罗轸为浙江都司断事,也是六品官。参照今天的行政级别,都相当于厅局级,对于乡野农夫,可是了不得的显贵。这其中固然有罗家弟子的奋斗,但张治的全力提携也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罗氏族谱中只是笼统地说诸多罗家子弟受教于张治而有了出息,并没有点破张治通过权力在帮罗家子弟进入仕途,想必是其中的内情也不宜宣扬,故而含糊其辞。
有趣的是,张治传世的《龙湖集》中,很少他和罗家交往的陈述,尤其是他母子乞讨、受罗瑶接济的事毫无踪迹,想来是涉及人生中一段比较尴尬的经历,故而回避,也可能是后人整理张治文集时,予以删除。不过,有两篇文章依然透露了某些信息。一篇是《赠李蕉溪序》,一篇是《愿乐亭序》。尤其前一篇十分明显地涉及与罗家的情谊:
予尝道湘中与罗氏兄弟游焉。罗氏居江水之曲,地奥而衍,每春涨水,沿溪入,平畴成浸,则系舟庭阶前。予时与罗氏兄弟鼓枻张乐,举酒食鲜,野翠交映,上下一碧,宛然坐镜中也。罗氏兄弟,与蕉溪李子秀夫称内兄弟也。尝语予曰:“蕉溪不妄言动,其中朴者也。”予缘是与蕉溪游。见其貌沌沌兮若澹,及发语,辄中理解。予亦信蕉溪朴者也。既而与湘之人士游焉,莫不曰蕉溪朴者也。甲午,蕉溪卒业于南雍。南雍之士亦曰蕉溪朴者也。辛丑,蕉溪以谒选至,相与道罗氏山水之乐,予心戚戚有湘中之思也。
张治受恩于罗瑶,同学于罗瑶子大钦、大宪等,为师于罗瑶诸孙,他本人说,与罗家有三世之交,他对罗家最大的感恩回报就是教诲提携罗家子弟。文章说,李蕉溪是罗氏兄弟的内兄弟,罗瑶第十代孙罗汝怀专门做了考证,得知李蕉溪便是罗瑶的女婿李钟,也在国子监就读而受谒选当官,任县丞,也是张治提携。张治在文章中反复强调李蕉溪的“朴”,似乎暗示,李蕉溪的才学并不出众,而是以质朴的品质受到赏识。在文章中,张治十分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罗家兄弟的交游,这都在印证世人的传闻。清代大儒王闿运在编撰《湘潭县志》时亦写道:“湘水有洲,曰古塽洲,或书作故磉。其南岸罗氏之世居也。明嘉靖时,富人罗瑶识张龙湖于贫困,洲皆官地,因龙湖贵势,乃得买焉,瑶葬于此。”也是一条佐证。罗氏家乘中还有张治给罗瑶长子罗大钦(三峰)写的一篇祭文,全文如下:
维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八月朔,越二十六日丁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以牲醴庶羞之仪遣奠于隐君三峰罗先生之柩。曰:予与三峰父子交三世矣,其间通好之勤,遗问之厚,情深契笃,有难以言尽者。昨闻三峰买舟北来,予甚喜。数年阔别之怀可一倾倒也。岂料舟至杨村,疾作而逝。呜呼哀哉!不远数千里而来,乃不能相见于二百里之外。岂其数欤?此予所以抱恨而长悲也。呜呼!三峰家累万金,子孙绕膝盈室。何乃客死旅邸,孤亲天涯?予为三峰益增嗟悼也。虽然天下之事无常,或安而窗下,或远而他乡,或行或止,或彭或殇,一定之数,人固不得而逃也。呜呼!三峰有知,其当逍遥大化之中,而委顺九原之下,临风遣奠,挥泪陈词。尚飨!
这篇祭文除了表现出张治对罗三峰去世的悲痛心境,还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第一,罗三峰数年不见张治,竟然乘舟北行数千里去探望京都的友人,与张治同岁的罗三峰这年已是62岁的老者,这一路的旅途风霜不难想见,结果病故在旅途,这种情谊的分量实在非同小可。第二,同年十月,即罗三峰去世后的两个月,张治也在京城病故,或许,这篇祭文也是张治的绝笔。因此,我们更能感受到张治与罗家的深情厚谊。如果再联想,还可以感受到张治虽然贵为辅臣,但在充满权谋机诈的官场上,他活得并不舒展得意,甚至很孤独,也许他生命中最温暖的体验还是和罗家三代人心心相印的交往。
这篇张治的祭文,未收入《龙湖集》,写作时间是张治去世前两个月,但罗家四修族谱才收集刊印此文,原因是社会上有在族谱中假托名人撰文的不良风气,罗家后人多有大儒,很忌讳作伪丑闻,故而非常慎重。咸同年间湖湘大儒,三峰公的第十代孙罗汝怀通过考证,认定祭文“真朴不似伪造也”。后来又有三峰公第十二代孙,也是湖湘大儒罗正钧进一步考证,他认为:“此文则初修谱三峰公实已嘱草,至北江公(罗枬)始成之。京师之行,虽访张文毅,而亦思求谱序于名公也。”即罗三峰千里赴京见张治,除了思念的原因外,还有修族谱求张治作序的意图。结果罗三峰和张治均突然病故,序未求得,只留下了张治写下的祭文。
于是,一个重要判断便呼之欲出:张治与罗家的交往是罗家显望的重要契机和条件。更直白地说,其本质便是权力荫护。尽管张治提携罗家子弟表面看是出于感恩和情谊,背后则是权力的支撑。显然,罗瑶家族仅有财富而没有权力护航,前途是不稳定的,罗家的显望与权力接轨,从而获得了持久性。罗瑶死后获得皇家表彰,诸位罗家子弟进仕入朝,其意义便在于此。当然,还要看到,和权力对接,还要经由一座桥,那便是取得相应的文化身份,最典型的形式便是科举进仕,这一点上张治时代的罗家子弟并不突出——缺乏举人进士,但在程序上,他们都经由张治的提携获得了国子监生的文化身份,获取了为官的门票。总而言之,文化资质和进仕为官合为一体,这是一个世家不可或缺的条件。张治正是在这个方面给罗家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而成为罗家的贵人。
细阅罗家族谱,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罗家以联姻的方式编织了一张非常坚韧的社会关系网。以罗瑶为例,其长子罗大钦娶了湘潭周环的女儿,于是,罗瑶就和周环成为亲家。这周环也是湘潭巨富,据说其田地分布四个县,从周家去州府,一路都是在周家的田界里行走。周环不仅是巨富,其家族方上周氏还有着厚实的权力资源。周环之后出了方上周氏六兄弟,均入朝为官,显赫湖湘,不妨简要介绍:周之屏,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官至布政使;周之翰,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举人,官至知县、四川按察佥事;周之光,官至知府同知;周之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官知府,户部主事;周之命,任府学教授;周之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官刑部主事。这种家族实力是罗瑶所不及且需要借助的。周环之女嫁到罗家后,地位很高,主持家政,可以想见,罗瑶和周环的联姻,对于家业壮大有着重要作用。后世罗周两个家族的姻亲关系绵绵不绝三百年,在湖湘家族之间的联姻史上,可谓罕见。
以联姻的方式壮大家族根基,这当然不仅是罗瑶的生存智慧,更显示出宗法社会巩固自身的基本策略,即以门当户对的联姻来扩张家族势力,建构利益共同体,直接效果是家族显望,间接或者说终极效果就是巩固维护宗法社会的长治久安。对罗家而言,这种联姻策略甚至比权力的持有更显重要。从族谱看,罗氏家族后人中并没有特别显赫的高官大吏,这意味着,靠家族子弟执掌权力来维护家族显望,罗家并非得天独厚,于是,联姻就成为弥补缺陷的重要手段。后续的历史表明,罗家维持家族显望,主要不是靠权力的直接占有,而是靠文化地位的声望,以联姻以及教育的方式,与权力群体构成了亲缘和师缘关系。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目中细说。
总之,罗瑶使家业富甲一方,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内阁大学士张治对罗家的权力荫护,使罗家后人读书进仕,走出湖湘,步入仕途,从而奠定了罗家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相应的文化话语权,还有和周家的联姻,也是同样性质。在宗法社会的时代,这都是家族显望的几个重要条件。当然,罗家与张治的相遇十分偶然,或称天意。不过,偶然中也有必然,就是罗瑶急公好义、对文教虔敬,所以才有资助张治读书之举。这又要说开一点了,中国传统历来重文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普遍的社会风习,罗瑶深受浸染。况且中国的文教与权力是孪生子,文教知识体系渗透着权力的诉求,所谓“学而优则仕”,这又是显贵之捷径。数百年鼓磉洲罗氏的族史也印证了这一点,罗家显要人物大都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依然孜孜以学,甚至弃仕而学,罗典就是典范。
细细辨析,五世祖罗瑶不仅成为鼓磉洲罗氏崛起的标志性人物,还以自己的实践提炼出了世家持续兴旺的路径——财富、文化、权力、联姻四位一体的诀窍。罗家后世正是沿着罗瑶开辟的道路而行,保持了500余年的显望。400年后,罗氏十六代孙,以考据著称的湖湘大儒罗汝怀满怀崇敬地书写了《重修鼓磉洲记》,便以罗瑶归葬鼓磉洲为理据,正式以鼓磉洲为罗氏命名:
古称湘水中四洲,见于晏殊《类要》,曰橘、曰直、曰誓、曰白小,鼓磉弗与焉。自吾始迁祖卜居其旁而洲始著,自吾五世祖讳瑶府君藏体魄其上,而洲获全也。
……考乾隆十九年,曾伯祖教谕君所为记,则墓已三修,迄五十余年再修,皆统言墓不言洲。宇宙久有此洲,独至道光中水患频乘,冲决溃裂,此岂昔之人所及料,而今之莫计于后者当何如矣。向者动费千缗,咄嗟立办,观者或叹其事之易集,即墓下子姓虽疲苶同弩末,而括其数约两千有奇,负郭之产犹累巨万,所居率多前朝旧宅,谓非祖之遗泽孔长欤?盖吾祖当前明正嘉间,义行甲邑里,如迁建今学宫,创置暮云官桥,出粟千余石实社仓赈饥,而亲邻待以举火者恒数百,提拔寒畯三十余人,而茶陵张公治位至台辅,其见于蔡宫詹扬宗所为表者,皆子孙所当敬念而则效。今跅弛者至荡佚不谋自给,其计身家者又往往以智力自雄,亦安知其来之有自?而吾祖之借手于来裔者,果后之人之能全其祖,抑祖之先有以自全也。
如今,六百余年过去,湘江依然北去悠悠,江心依然屹立鼓磉之洲,桑园葱茏,依然簇拥肃穆的罗瑶古墓,两岸罗家子孙已繁衍达七万余人。
|
 罗氏留言
罗氏留言  罗氏论坛
罗氏论坛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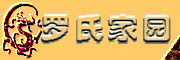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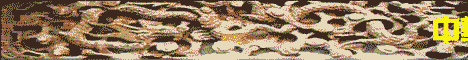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传承
罗氏传承  罗氏文苑
罗氏文苑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