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祖江西来
作者:罗 宏http://www.luos.org
洪武初年,江西通往湖南的条条山路上,人流漫漫。北望长江,首尾相接的舟楫,溯流而抵洞庭湖。
这是一次改变湖南历史的最大规模移民迁徙。
史称江西填湖南。
放开眼界,还可看见波及大半个中国的背井离乡景象。
这是由政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中华大移民。元明之交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狼烟遍地,天灾连年,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十室九空。明太祖朱元璋在一片血火中定天下,立即公布了“招徕流亡,鼓励垦荒”的国策:“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以为己业……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王勇著《湖南人口变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是,一首民谣流传至今: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从明代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约50年间,明政府先后18次从山西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经洪洞县大槐树处办理手续,发放“凭照川资”,强制性地向全国广大地区迁徙人口,迁入地涉及18省500余县,主要为地广人稀的中原地区。移民比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以洪洞为迁徙出发地的移民达百万,覆盖880余姓,移民后裔过亿人。这次大移民世界罕见,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深远,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华儿女魂牵梦萦的祖居地符号,也成为明代大移民的民族集体记忆。
其实,洪洞大槐树的集体记忆并不能精确勾勒明初大移民全貌。据《简明中国移民史》提供的研究数据,明初移民有遣送、军屯、商屯、民屯等多种方式,长江流域的移民规模700万,华北地区移民规模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20%。
显然,只有在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透视江西移民的进入湖湘,才能更深刻地意会其史诗品质。宋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西的经济、文化跃居全国领先地位,更是人口第一大省。元代初年(1290)江西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1/4,超过当时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总和。同期湖南人口约570万,约为江西省的1/3,就土地面积而言,湖南还多5000平方公里,更显两地人口密度差距。直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已经推行了20余年,江西人口密度依然有每平方公里49人,湖南仅10.6人,江西人口密度是湖南的4.6倍。且不说政府着眼于全国政治、经济战略布局推行大移民,仅从毗邻的江西与湖南的人口落差,也可以感受到江西填湖南的移民动力。
不能忽略元末战乱。有学者认为元代湖南的户口统计有许多遗漏,进行了更精密的估算,得出元末湖南人口达到1000万,而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间的湖南人口约为184万的结论,这意味着战乱天灾导致明初湖南人口锐减了近82%,如果考虑到此时江西填湖南的移民增量,元末明初湖南人口锐减了85%当不为夸张。《醴陵县志》载:“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有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湘潭《石浦王氏族谱·良远公家传》也记载,洪武初年,“太祖命郡县叛服不常者,皆屠戮。湘潭于元至正时已归附,士民安堵如故。后指挥饶广叛,胁民以从己。太祖命营阳侯杨璟讨诛之,遂屠湘潭,无遗育。存者唯七姓,姓各一人,亦逃匿,仅而后免”。至于民间传说中,各种朱元璋血洗湖南的版本更是绘声绘色。灭门的屠杀,使富庶的湘东(中)沦为荒芜之野,也给新的垦殖创造了无限可能。加上此时江西业已沦为官吏盘剥百姓的重税之区,连朱元璋都感叹:“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
苛政猛于虎,即使政府不强制要求,江西之民也会蜂拥奔逃至湖湘。
土地,大片肥沃而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和背井离乡的勇气,召唤着漫漫人流寻梦湖湘。史料显示,明代移民湖湘的家族达3010支,为历史上迁入湖南移民家族的一半以上,尤以明初为移民高峰期,达1518支,其中江西移民达1202支,约占80%。《湖南通史》认定:“在明代的湖南居民中,土著已是少数,而外来的,特别是江西移民成为主要组成部分。”
所以今日之湖南人,大都可以像山西洪洞走出的移民后裔,东望江西,唱着乡愁绵绵的歌谣,缅怀自己的大槐树。
最早关注江西填湖南现象的大概是顾颉刚的高足谭其骧。他在学生时代写下了著名论文《湖南人由来考》,得出了明代以后湖南人大都来自江西的结论。沿着这个结论寻觅,还有更多的历史与文化之谜有待破解。有学者考证,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有近60万,亦有移民百万之说,我们不禁联想,洪洞移民百万,分布中国18省,而60万或百万江西移民,该会带来怎样的社会裂变?再如,江西填湖广是东西路向,改变了历代移民的南北路向,这又意味着什么?就湖湘而言,在明代可说发生了人口族系性的断裂,至少也可以说大换血,这又意味着什么?人口不是牲口,是烙印着文化的生灵。它意味着崛起于宋代、辉煌于宋明,文化巨匠星汉灿烂,且为理学重镇的赣文化,和同样开化于宋代、以理学为旗帜的湘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大融合。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赣文化明末而衰,湘文化却由于王夫之的出现,在清代达到了主宰中华的辉煌,这是否暗示某种文化传递和转移呢?如果有人断言,明后的湖湘文化实际是赣文化的赓续,并非武断。
赣文化和湘文化,有着太多的关联性。
和湖南一样,江西在宋代以前,没有多少本土性的文化大名家可以炫耀,晋代江西出了陶渊明,可他生前默默无闻,按余秋雨的说法,是到了宋代因苏东坡的大力推崇,陶渊明才赫然为世人所知。江西享誉中华的文化辉煌是在宋代掀开扉页,而湖湘的文化大开化,也是起于宋代理学的湖湘进入,一旦提及理学的湖湘进入,江西和湖南文化间就构成了某种师承关系。
理学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形态,是中国主流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最为精致、完备的理论成果,曾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这些自不必多说,尤值得关注的是,江西是理学思想家们云集之地。翻阅《哲学大辞典》可见,收入辞典的宋明时期江西籍哲学家竟达50人之多,占同期中国哲学家的1/6,可谓奇迹。因而江西被称为理学创构和完成的摇篮之地应不为过。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四大宗师,以及吴澄、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理学大儒构成了薪火相传、各有建树、蔚然壮观的理学家群体。他们大都为江西学人或宦游江西,在此悟道讲学,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从而使理学思想大厦与江西水土相互依存,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理学即江西理学。所以,对理学的建构是江西学人最骄傲的文化勋业,毗邻的湖湘对理学接纳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江西的理学播扬与辐射。
崛起于宋代的赣文化另一个奇迹是教育,突出的表现又是以书院为特色的教育,这又与湖湘文化大开化以教育为先导且以书院兴盛的特点相契合。江西和湖南的书院均领先于全国,但二者比较,江西更胜一筹。资料显示,北宋全国书院73所,江西有23所,而第二名的湖南才9所(一说12所);南宋全国书院442所,江西147所,约占33.3%,第二名浙江才82所,第三名湖南约为70所;明代江西书院238所,湖南书院124所,也在江西之后。这意味着湖南的教育与江西的教育有相当的差距性。与教育兴盛密切相关的是科举业绩,两者比较起来,落差更明显。资料显示,唐代科举进士总数7448人,湖南25名,占比为0.33%;宋代进士总数32000人以上,湖南达908人,跃居全国中游水平,占比约为2.8%。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和江西比就汗颜了。宋代江西出了5142名进士,占比约为16%,到明代,进士总数为24595人,江西中进士高达3418人,占比为13.8%,湖南进士556人,占比约为2.3%,湖南科举业绩明显下滑。就科举的巍科(即科举考试名次靠前者)进士而言,江西更显优势,明代江西巍科进士达85人之多,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官至宰辅的达22人之多,仅次于浙江的26人,为全国第二,故明代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教育的领先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江西人口文化素质普遍高于湖南,因而江西移民的进入湖湘,肯定会拉动湖南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这种提升又会拉动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嬗变。
再看文史科技大家的风景,江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王安石、晏殊、晏幾道、欧阳修、李觏、曾巩、黄庭坚、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汤显祖、马端临、刘恕、刘攽、汪大渊、朱思本、张潜、宋应星等在文学、史学、科学等领域均为领袖巨匠,以至于在江右地区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新高地,仰望江西成为时代风尚。总之,江西填湖南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土地居留的变迁,而应理解为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甚至可以联想到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对美洲的大移民。诚如湖湘学者唐浩明所言:“明初,湖南人的组合发生过一次大变动,那便是数以百万的江西人西移三湘。赣人入湘,不仅因血统较远的联姻改善了湘人的体质,还因为北宋以来两赣文风盛于湖南,从而将一种人文优势带进湖南。”(廖静仁主编《天问湖南·历史之旅卷》)
20世纪30年代,燕大学生谭其骧发表论文《湖南人由来考》,指出了大多数湖南人祖籍江西的史实,主要依据的是家谱记叙,有学者认为其家谱资料收集不全,且多为世家谱系,缺乏对普通民众族源的调查资料,因而结论不够稳健。但这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具有移民背景的族群移民湖湘后,往往有发达的生存前景。2006年,湖南官方启动了湖南文史典籍《湖湘文库》的编撰,对湖湘文化世家专门进行了总结,梳理出45家湖湘文化望族世家。它们有两大特点:第一,绝大部分世家显望于清代;第二,几乎全是移民家族,且江西籍最多。这似乎表明,移民家族更具精英性,对湖湘文化的引导性更强。罗宏和许顺富合著的《湖南人底精神》对此现象做出了阐释:
移民群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甘现状,敢于冒险,富有开拓精神。这个群体的湖湘进入,一方面带来了外部世界的视野和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本土居民的见识,也把开拓精神植入湖湘,他们来湖湘就是来开拓创业的,和湖湘本土民性中的霸蛮血性相融汇,使湖湘文化中的进取性更加富有生机。我们重点讨论的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之后。周敦颐、王夫之、李东阳、陶澍、贺长龄、魏源、罗典、何凌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李续宾、刘长佑、王闿运、王先谦、王壮公等等均是。这也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成为乱世英雄、扭乾转坤的时代英杰的重要奥秘所在。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观察一个江西移民家族个案,才能体会到叙述的史学价值。事实上,我们期盼一叶而知秋。
那就进入个案审视。
大约明洪武二十年(1387),一位江西豫章(今南昌)青年农民,在移民大军中风尘仆仆地向湖湘走来。他肯定不会吸引史学家的目光,因为此时,他仅20岁,是江西吉水县的农民,叫罗应隆。跟在他身后的是生死相依的妻子邹氏。这位女人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在蠕动。他们一路上发生的故事已不可考,我们确知的是,夫妇俩筚路蓝缕地来到湘潭地界,罗应隆在湘江边停住了迁徙的脚步,久久瞩目江心一条狭长的洲岛——鼓磉洲。尽管芳草萋萋,一片荒凉,颇通堪舆门道的罗应隆却一眼看中了这片视野中的风水。就在凝望时,他怀中揣抱的先祖灵牌也突然显得如铅块一般沉重。他心一动,扑通跪下,朝东方磕拜祈祷,开始卜卦,结果神示说,这将是他及子孙兴旺发达之地。他又惊又喜,立即和妻子卸下简单的行囊,在鼓磉洲南岸江畔一个叫鹧鸪坪的地方搭起了窝棚……
一对外来夫妇的艰辛创业就此启动。第二年,儿子源佐出生,罗家有了第二代,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悄然掀开。
《鼓磉洲罗氏族谱》初修成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秋,距始祖罗应隆迁湘已经170余年。岁月的淘洗使许多记忆遗忘,谱中只记录迁湘始祖罗应隆于明洪武元年(1368)生,祖籍江西吉水,字世兴,号政斋,郡望豫章罗氏,原配邹氏,子一源佐,夫妇生平和享年均不详。尤其是罗应隆的父脉没有记载,给后裔子孙留下了困惑和遗憾。不过后世族谱有这样的记载:“继宋而明,适吾湘之族所由基始也,时整奄、一峰诸公先后振兴江右,而吉水亦多名人,吉水又吾族之始所由以始也。”还有这样的记载,清乾隆年间,江西吉水罗氏族人曾奉明大儒罗洪先遗像来湘潭,以供应隆公后人家庙供奉,遭到婉拒。应隆公后人称,非不认远祖,乃不敢掠美远祖荣耀也,鼓磉洲罗氏当自立自强,争得家族荣光。由于罗洪先是秀川罗氏一脉的大名人,罗应隆当为秀川罗氏后裔。
综合家谱史料,可以这样描述,罗应隆源自豫章罗氏,江西南昌地区一个显赫的江右民系家族。《江西通志》载,汉高祖时灌婴带大将罗珠平定豫章,罗珠立功,封大农令,后人居豫章。至汉景帝设豫章郡,环城种樟树,其子孙名人辈出,遂被称为豫章罗。民国学者罗元鲲考证,罗珠“实为罗姓鼻祖,分布天下者皆其后也”,这未免有些武断,史学家、谱牒学家罗香林的说法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唐宋以还,豫章支派,独为最盛,渐著籍虔、吉、汀诸州。元人侵宋,始祖率迁粤……布于各邑,蔚为名族,其间达士闻人,不可殚述。”细分一下,豫章罗氏又衍化出许多分支,罗应隆当属豫章罗氏吉水支系,始迁祖罗为罗珠三十四世孙,唐代进士,官至吉安刺史、工部侍郎、节度使,罗后人同样英杰辈出,鸿儒硕彦罗钦顺、罗伦、罗洪先、罗大经等均属此系。概括地说,豫章罗珠—吉水罗—湘潭罗应隆,这是罗应隆一族由汉代至明代基本的传承脉络。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罗应隆迁湘后,其垂直父系出现了姓名遗忘。家族观念极强的中国人不该出现这样的遗忘,况且是背井离乡的游子,更何况罗应隆通晓堪舆门道,可谓近神之人,这样的失误断难发生。那么,他自小就是孤儿吗?还是生命中遭遇了不测,以至于来不及留下父祖的名姓?我们注意到,罗应隆是独子单传,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英年早逝,所以,许多应该记忆的先人故事,也就随着他匆匆离世的脚步湮没。这大概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有趣的是600年后,后世修谱人却在衡山罗氏族谱《小山房谱》中发现了一些文字,似乎可以弥补鼓磉洲罗氏族谱中始祖罗应隆祖脉断裂的缺憾。《小山房谱》大意是这样说的,吉水罗一脉传至二十一世孙罗朝,当时是元明之交,大规模的江西填湖南移民潮启动,罗朝是个江湖郎中,迁入湖南衡山,入赘董氏,成为衡山罗氏小山房始祖。朝公有六子:应隆、应海、应宗、应升、应亮、应荣。族谱明确记载:应隆,生于明朝洪武初年,卒于洪武三十二年(1399),迁湘潭鼓磉洲。这些记载与鼓磉洲罗氏族谱中关于始祖罗应隆的记载有多处吻合。于是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喜的猜测:罗应隆之父当为罗朝,迁湘的路径也是先迁湖南衡山,再由衡山迁湘潭,而且罗应隆享年32岁,确是英年早逝。以上考证见于2010年后新修的《鼓磉洲罗氏十修族谱》。从考证者的态度和分析看,这并非完全臆断,可成一说。问题在于,罗应隆是否为衡山小山房始祖罗朝长子,以及他是否从衡山转迁湘潭,还不能因此得出定论,尤其是罗应隆享年32岁,属于英年早逝,虽然从罗应隆只有独子看,早逝亦有合理性,可罗应隆的嫡传子孙均不知始祖享年,数百里外旁系的衡山小山房罗氏修谱人又如何得知?
说这些只不过是做一些家族渊源的梳理与猜测。其实对迁湘的罗应隆而言,其生命意义并不在于显赫的郡望,而在于独立开辟了一支湖湘罗氏。可以想象,罗应隆通堪舆之道,多少有家族书香风气的传承,包括毅然背井离乡,也需要胆识与憧憬的激励,甚至可以猜测,他是一位粗通文墨、精明强干、富有血性胆气的乡村农人。这对于开拓一方家业,无疑是必要的秉赋支撑。《鼓磉洲罗氏族谱》及地方志的记载显示,经历了五代人耕耘,鼓磉洲罗氏开始在湘中大地显耀。江西移民罗应隆的后人成为不可小觑的湖湘望族。
明清以来,鼓磉洲罗氏族中文武英杰辈出,见于史志记载近百人,绵延不绝500余年。据清代《湖南通志》统计,清代湘潭入志的名人350人,比省城长沙还多百余人,为各县之首。分75姓,张姓名人最多,为26人,罗姓名人居次,为22人,周姓名人18人,位居第三。但张、周二姓名人并非一族,而罗姓名人基本为鼓磉洲罗氏,这样算,罗氏当为湘潭载入史志名人最多的家族,况且《湖南通志》遗漏数位罗氏名人,补缺后罗氏名人可达26人,与张姓并列第一,而且文武双全,更是第一显族。罗瑶、罗栋、罗轸、罗枬、罗玑(斗寰)、罗熙、罗升、罗典、罗云皋、罗修源、罗汝怀、罗德煌、罗逢元、罗萱、罗立德、罗经德、罗启勇、罗春鹏、罗永泰、罗正钧、罗正纬、罗正璧、罗暟岚等均为湖湘名士或湘军骁将。还有罗学瓒、罗哲等现代革命烈士,可谓生生不息……
于是,罗应隆也就获得了其史学身份:他作为江西填湖南历史大事件中的普通一员,筚路蓝缕地建立了鼓磉洲罗氏一族的原始基业,尽管英年早逝,尽管也没有创下多旺的家业,甚至可以说,他的家族贡献仅限于繁殖,却因为后代儿孙英才济济,家族后裔500余年显望而享有一脉湖湘世家开基始祖的荣耀,且受到子孙后代的顶礼膜拜。这便是历史的诡异之处:某些人并不需要大智大勇,并不需要功业盖世,他只需要迎合历史潮流,稍稍向前走出一步,就足以青史留名。比如罗应隆,就是从江西走到了湖南。
罗应隆的许多后代子孙则以另一种途径进入了历史。
于是,数百年湖湘风雨扑面而来,潇潇风雨中便回荡着鼓磉洲罗氏儿女的激越呐喊。循声聆听,你会发现,他们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彰,或以文章、隐德著,但都可以归结到重实务、敢担当、崇文教、讲节操的基本人格风采,这种人格风采里既是儒家文化的传承,更是湖湘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湖湘文化是对儒家文化最具血性也最具务实性的践行,化作罗家子弟的为人处事,成就了罗氏家族的种种湖湘业绩。因此,罗家故事也是湖湘的故事。它如一扇窗口,透射出近代以来湖湘大地的风云气象,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生动注脚。对于湖湘文化,学者有多种概括,最有概括力的当属王夫之的“豪杰”说,即乱世受命、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人格情怀。细细咀嚼,你会深深感到,近代以来的湖湘英杰,有着浓烈的救世痴迷、政治痴迷、道德痴迷、斗争痴迷,从而构成了激进与保守、建设与破坏都堪称极致的湖湘文化人格。对此,见仁见智,尽可百家争鸣,但不可否认,近现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在湖湘文化意志中展开,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成也湖湘,败也湖湘。因而,如果缺少对湖湘的文化审视,就可能进入历史迷途。所以,有关湖湘的文化观照,远远超出对地域的文化研讨,而提升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拷问。况且,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族并非仅仅是血缘集合体的存在形态,它还昭示着一种社会的结构形态,甚至是一种政权形态。以皇权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和单一,效忠帝王的官僚体制及至郡县就戛然而止,县下的广大乡间则是家族的自治区域,从而构成了皇权与族权联合执政的国家形态,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变,都是皇权与族权的政治协商结果,而大家族,往往是这种政治协商的民间代表。总体而言,族权对于皇权是拥戴和顺从的,但并不排除族权和皇权之间也存在博弈。在博弈中皇权的妥协并不鲜见,这就意味着,皇权的任性受到了很大制约,反之亦然。于是古代中国就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制约机制,遏制绝对权力造成社会灾难。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朝官但凡遭遇了委屈,往往挂冠而去,走得十分决绝:朝廷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有留爷处,就少一些奴气,多一些潇洒和尊严。至于风烛残年,也可以告老还乡,叶落归根,因为家族的门永远为游子敞开。于是,先人们如此那般存在,而后人却不能如此那般存在,也就有了各自的理由。于是,我们对罗家的叙述,也就蔓延出了超越家族故事的意涵。
时移世易,传统的家族时代已然远去,后人还须前行,只有知晓先人存在的理由,才能更确切地判断自己存在的依据。无可讳言,后人对先人怀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深情的祭奠是为了豪迈的诀别,超越先人,才是后人走出湖湘,继续祖先寻觅的抱负。既然600年前,这个家族的始祖能够走出江西,开创湖湘的家族新业,那么600年后,这支家族的后人,为什么不能走出湖湘,融入新的时代气象之中呢?马克思说过,死人的复活是为了未来的存在。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眸这个湖湘家族的足迹,也正是我们的期盼。
|
 罗氏留言
罗氏留言  罗氏论坛
罗氏论坛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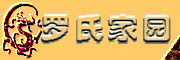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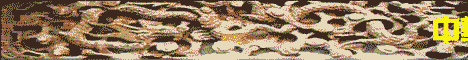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传承
罗氏传承  罗氏文苑
罗氏文苑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