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唐五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与敦煌罗氏家族研究
作者:王腾http://www.luos.org
〖按〗姓氏的族属和文化认同并非同一概念。本文中,王腾将内迁的西域罗氏归为吐火罗势力圈说、粟特系统说、印度说、于阗说四类,再加上鲜卑、突厥和汉族的罗氏,足见罗氏的族属极为复杂,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姓氏,是真正的“中华一脉,渊远流长,包罗万象,有容乃大”。
在中外关系史和敦煌学的学习中,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外来居民流寓中国的情况,如何分辨清楚这些历史人物究竟为本土居民还是外来裔民呢?这涉及到胡姓、胡名的问题,“罗”氏存在以上情况,能够作为个案来分析。在隋唐五代文献中可以见到一些罗氏人物,其中有中原罗氏,如罗艺(襄州襄阳人)、罗士信(齐州历城人)、罗道琮(蒲州虞乡人)、罗弘信(魏州贵乡人,原为豫章罗氏)、罗绍威(洪州豫章人)、罗廷规(洪州豫章人)、罗周敬(洪州豫章人)等;同时也存在西域罗氏或其后裔,如罗含(中亚人)、罗真檀(护蜜国人)、罗友文(护蜜国人)、罗全节(骨咄国人)、罗世那(胡人后裔)、罗易没(胡人后裔)、罗伏帝延(胡人后裔)等。笔者翻阅了数十种隋唐五代文献,并把西域罗氏及其后裔罗列出来且加以分析,以求分辨清楚隋唐五代西域罗氏及其后裔流寓中国的史实,这在中外关系史和隋唐五代史以及敦煌学中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正式行文之前,有必要把“西域”和“中国”两词作一说明。西域的范围随时代的不同而经常会有所差别,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方;广义的西域,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方,除包括狭义的西域以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的一部分。本文的“西域”特指广义的西域,指隋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方。与之对应,“中国”的范围在历史上也是各个时期多有不同,本文所指的“中国”特指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原王朝,根据文献所见西域罗氏流寓的中国地方主要是长安、洛阳、敦煌和吐鲁番等。本文以出土文献和传世史乘为材料来说明西域罗氏流寓中国的情况,有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姓氏书中所见罗氏源流
为了说明西域罗氏及其后裔流寓中国的情况,有必要辨清各类姓氏书中所见罗氏源流支脉。“罗”姓在《百家姓》里面有记载,是一个较为著名的姓氏。笔者在翻阅隋唐五代文献时,见到其中有一些流寓中国的罗氏,此罗氏是否为西域罗氏,与中原罗氏有何关联?我就《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通志》、《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寰宇记》等传世文献以及敦煌文书S. 2052、北图位79号( 8418)等出土文献中涉及到罗氏的部分分类排比如下,以探求罗氏,主要是中原罗氏的源流。
在传世姓氏书中,岑仲勉先生据《元和姓纂》所作的校记云:“罗氏有齐郡,襄阳、河东三族,此亦洪氏据秘笈新书所补。”[1]郑樵《通志略》记载:“罗氏:子爵,熊姓。一日祝融之后……周末居长少(作者注:应为”沙“字)……襄阳记有罗象……又叱罗氏改为罗氏。五代有罗绍威。望出豫章长沙。”又云:“罗氏有二。口姓之后。以国为氏。又有叱罗氏改为罗”及“叱罗之为罗”[2]。<魏书·官氏志》日:“叱罗氏改为罗氏,[3]。《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二记载:“罗”姓“唐益州蜀郡三姓,洪州豫章六姓,皆其一也”[4]。在出土文献有关姓氏书的记载中,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云:“洪州豫章郡出八姓:罗、雷、熊、除、璩、谌、洪、口”[5],另一份敦煌卷子北图位79号( 8418)《姓氏录》则记载:“豫章郡五姓:洪州:熊、罗、章、雷、谌”[6]。在《太平寰宇记》中对于罗姓的记载和北图位79号( 8418)《姓氏录》的解释并无二致[7]。
根据以上记载罗氏有豫章、齐郡、襄阳、河东、蜀郡等几支,以及胡人叱罗氏改称罗氏。另外《汉书》、《万姓统谱》、《晋书》、《尚友录》、《南史》、《魏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十国春秋》、《长汀县志》、《沙县志》、《淄川县志》、《延平府志》、《泉州府志》、《武冈州志》、《广东通志》等文献记载中的罗氏人物[8]大多数是中原罗氏,只有北朝时代人罗结、罗斤、罗敦、罗拔、罗提、罗弥、罗伊利、罗道生、罗云、罗阿奴、罗延、罗盖、罗杀鬼、罗鉴、罗衡、罗念一族应为胡人及其后裔,据以上有关姓氏的典籍,似乎应为叱罗氏改称罗氏的例子。以上诸位罗姓人物生活历程也很难与西域罗氏发生联系。
综上所述,根据各种姓氏书的记载可知罗氏有中原罗氏和胡人改姓两种,其中前者又有豫章、齐郡、襄阳、河东、蜀郡等几支,后者有胡人叱罗氏改称罗氏一说;从姓氏书的记载中很难发现西域罗氏流寓中国的根源,但是从其他文献中却能找到西域罗氏的踪迹,尽管这种行踪影迹不太明显,但是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后文就以各类隋唐五代文献来分析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
二、有关西域罗氏的学术史
关于西域罗氏的问题中外学者多有涉及,只是多为几笔带过,少有详细考辨。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罗姓者有印度人罗好心,也有鲜卑出身者[9]。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论述了流寓长安的西域人,他指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提到了不少中亚人,据碑文,圣历、先天之际,有景教僧首罗含,向达先生把其定位为中亚人,并认为即Abraham的对音[10]。刘铭恕先生在《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一文中对所见的罗氏材料加以分析,认定罗氏为吐火罗人[11]。桑原骘藏先生在《论隋唐时代来往于中国的西域人》一文中举述西域罗氏认为其源流是印度人(可能源于Kumara的略称或西印度地名Lara[ Lata])和鲜卑人(叱罗氏改姓)[12]。石田干之助先生的《天宝十载丁籍所见敦煌地区的西域系统居民》一文认为罗姓为胡姓[13]。池田温先生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中分析了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论述了敦煌的祆神事宜,对从化乡居民的户口数、姓氏、名字、家庭形态、公务负担、身份构成等作了分析,比较了从化乡与其他各乡在差科簿上的差异,并对聚落的位置,居民的生业,聚落的由来,聚落的机能及其演变,聚落的消亡等问题一一论述;值得重视的是,池田先生在分析差科簿中从化乡的居民姓氏、名字等问题时,对西域罗氏的来源也有所论述,他认为吐火罗势力圈内的人们多以“罗”为姓,从而推断罗姓应与吐火罗、睹货罗国(TokhareS. tan)具有关联;然而池田先生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在此文的论述中不时把罗氏人物归类为粟特,使人莫衷一是;同时这位东洋汉学界的名家指出胡姓问题极为复杂,不能等闲视之,充分显示了池田先生治学的严谨;此文在中外关系史和隋唐五代史以及敦煌学的学术史上地位不凡、举足轻重[14]。蔡鸿生先生在其《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曾经对唐释圆照撰《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尚上表制集》卷二中的一条材料进行分析,进而认为材料中的五个人未在唐朝境内落籍或寄住,大概是新人境的中亚移民,并推断罗姓者可能来自吐火罗[15]。姜伯勤先生在分析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时,也对差科簿中从化乡的罗氏作了解说,他认为罗氏或系粟特南方相临的吐火罗(睹货逻)国所出身,从化乡的居民一部分是由吐火罗方面移住的伊兰民族乃至其后裔[16],姜伯勤先生在这里指出“后裔”,颇具历史感。以上池田先生以及姜先生的论著又对从化乡罗姓名字的对音问题作了陈述,补充了从化乡罗氏为西域罗氏的证据。郑炳林先生在其《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一文中把罗、翟、贺诸氏认作胡姓并与安、康、石、史、曹、米等粟特姓并列[17]。陆庆夫先生在《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一文中把罗姓明确断定为吐火罗姓,属于中亚胡姓[18]。然而郑炳林先生、陆庆夫先生在其有关论述中又把罗氏视为粟特人或粟特裔民来使用[19]。荣新江先生在其《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中认为《罗甑生墓志》中的罗氏可能为胡人后裔[20];笔者曾向荣先生请教有关西域罗氏源流的问题,他认为流寓敦煌的罗氏可能是粟特系统的后裔,但也不排除是吐火罗后裔的可能性。冯培红先生也曾就西域罗氏的源流问题多次教示笔者,他认为西域罗氏可能源出吐火罗,存现于中国的西域罗氏为吐火罗人后裔。
三、隋唐五代文献所见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考辨
西域罗氏在隋唐五代文献中所见不多,为了说明西域罗氏流寓中国的情况,笔者翻阅了几十种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相关出土文献以及传世史乘,应该说关于西域罗氏的材料比较匮乏,能够直接证明罗氏自西而来的材料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很难用某支罗氏的家族史来分析西域罗氏在中国的历史状况;下面是笔者在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隋唐五代出土墓志以及《册府元龟》、正史等文献中找到的与西域罗氏有关的一些资料,并对下列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因为这些资料是支离破碎、互不统属的,无系统性可言,所以最终只能说明西域罗氏存现中国的大致轮廓,难以窥得全貌。
(一)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西域罗氏
下面笔者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材料说明西域罗氏存现于中国的情况。
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记载:
l.马一匹骝敦六岁
2.开元廿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十 八
3.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
4.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
5.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
6.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7.练主
8.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卅四
9.保人兴胡罗世那年卌
10.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卌五
II.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21]
这是一件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的契约文书。契约的各个要素相对俱全,有正文(买马事件),有交易双方(练主、马主),有保人(三名),有交易的具体时间(开元廿一年正月五日)。文书的内容是有关西州百姓石染典用大练于开元廿一年(733)正月五日在西州市买康思礼的马匹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一应俱全。交易为物物交换,以练换马匹,这说明在唐朝的西州存在经济交换的早期形态——物物交换。这件契约文书有一处很有意思,即“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颇有地下交易的味道,对各种结果考虑得很周到。
与本文有密切联系的是这件契约文书涉及的五个人物:石染典、康思礼、罗世那、安达汉和石早寒。这件文书出自吐鲁番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马匹交易地点在西州市,石染典、石早寒注明为西州百姓且石、康、安和罗诸姓西域皆有,九姓胡姓中有石、康、安,罗姓亦为西域胡姓所有,这些信息使人们有理由怀疑石染典等五人有可能为西域胡人后裔。引人注目的是罗世那和安达汉两人前面注有“兴胡”二字,“兴胡”的含义学者已有解释,朱雷先生认为“兴生胡’即‘兴胡’,乃兴治生产,经商求利的商胡”[22];陆庆夫先生说:“‘兴胡’即兴生胡,谓兴生贸易的胡商,多指昭武九姓人”[23程喜霖先生则对“兴生胡”的含义作一解释“指西北少数民族以市易取利的商人,尤以昭武九姓商胡最著名”[24对于“兴胡”的解释,羽田亨、姜伯勤等先生亦有论述[25];尚衍斌则认为“兴胡”具有“兴生贩货,无所不至”的特点,并且为兼营高利贷的胡人[26]。综上各家的观点,“兴胡”为西域商胡,尤指九姓胡。那么,这件契约文书中的“兴胡罗世那,兴胡安达汉”皆为西域胡人后裔,这也为把“石染典、康思礼、石早寒”定位为胡人后裔增加了可能性。另外,“安达汉”的“达汗”应为胡名,取自突厥二十八等官号,即Tarqan,是胡名中突厥成分的显现[27]。从语言学方面诠释名字,更加大了上述人物为胡人后裔的依据。罗世那为胡人后裔,说明吐鲁番文书中存在西域罗氏,尽管材料不多,却弥足珍贵。
这里还有一条材料,同样出自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
(前缺)
6.开元拾玖年贰月 日,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
7.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疋。某婢及
8.练,即日分付了。请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问口承贱
9.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伍人款,保不是守寒良该诱
10.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
11.练主
12.用西州都督府印 婢主兴胡米禄山
13.婢失满儿年拾贰
14.保人高昌县石曹主年卌六
15.保人同县曹娑堪年卌八
16.保人同县康薄鼻年五十五
17.[同元]保人寄住康萨登,年五十九
18.保人高昌县罗易没年五十九
19.史
20.丞上柱国玄亮
21.券
22. 史竹无冬
(后缺)[28]
这也是一件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契约文书,同上一件一样,也有正文(买卖奴婢事件),有交易双方(练主、婢主),有保人(五名),有交易时间(开元十九年)。其内容是有关唐荣用练易婢事件,时间为开元十九年(731),地点为西州市,交易亦为物物交换,以练买婢。
在这里依旧分析一下人物的姓名,其中出现的人物有:米禄山、失满儿、唐荣、石曹主、曹娑堪、康薄鼻、康萨登和罗易没。从名字上分析,失满儿为胡人的可能性较大。曹和康两姓皆为九姓胡姓所有,且禄山、娑堪、薄鼻、和萨登诸名胡风色彩严重。从语言学上讲,“禄山”作为一个吉祥的词语,源远流长,它是译音字,源出波斯语roxS. an,后从波斯语转入粟特语,从贵族流人民间,意为“光”、“明”,这一词在胡名中有很高的复现率。[29]公元前四世纪初亚历山大的王妃大夏公主,就曾用过这个名字[30众所周知,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也使用过这个名字;还可以找到的证据是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大量出现了这种胡人的名字。这件文书中“米禄山”三字前面出现了“兴胡”一词。因此,以上五人(米禄山、失满儿、曹娑堪、康薄鼻、康萨登)似应为九姓胡人后裔;石曹主是否为源出西域的胡人裔民,不能肯定,但是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大概可以推测这是一件与胡人裔民群体有关的契约文书。下面分析一下“罗易没”这个人物,罗姓源流众多,有来自于西域的一支。从名字上分析,把“易没”之名解释为胡名比释为汉名更加妥当,罗易没与上述九姓胡人裔民同在一件契约文书中,紧密相连,况且兴胡米禄山请罗氏人物作为保人,足以显示兴胡米氏对于罗氏的信任,这种信任似乎可以从他们同为胡人这一方面来诠释,这样就增加了罗易没为西域胡人后裔的可能性。至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似应为汉人,这样这件契约文书可以理解为胡汉经济交流的例证,只不过这种交流是买卖奴婢,实在难称高尚。
下面一条出自吐鲁番文书中的材料也有罗氏的踪迹。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
(前略)兴胡史计思作人史胡煞 羊二百口牛六头别奏石阿六作人罗伏解驴两头(后
略)[31]
这件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的文书提供了这样一份名单:史计思、史胡煞、石阿六和罗伏解。史计思前有“兴胡”二字,据前分析,应该视为胡人后裔无疑。石和罗姓皆为西域诸姓所有,这几个人疑为胡人后裔;更兼胡煞、伏解诸名胡风色彩突显;又增加了史胡煞、罗伏解为西域胡人裔民的可能性。罗伏解前有“作人”二字,据朱雷先生指出,高昌“作人”是一种与南朝“十夫客”相似的劳动人手。[32]由此可见:西域罗氏中有沦为下层劳动人民的人物。在西域这样的胡人聚居区,西域罗氏与其他胡人在一起的史实应该常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留存至今的资料并不太多,而且由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西域出土文书记载不详,这为后人分辨清楚罗氏的真实来源增添了不少困难。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件给后人提供了罗氏和史氏、康氏在一起的材料。阿斯塔那512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都督府史康柱欢等残牒》文书残缺不全,给研究者带来了不少困惑,但它提供了“罗中郎”、“史口口”和“康柱欢”等人物[33]。罗、史和康诸姓都为西域胡姓中所有,况且三姓人物同在一起,使后人怀疑他们有可能为西域胡人裔民。
在探讨西域罗氏的问题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条关于“罗寺”的材料,应引起后人的重视。阿斯塔那155号墓出土的《高昌某年传始昌等县车牛子名及给价文书》中记载:“(前略)罗寺道明车牛一具,得银钱三十九文。(后略)”。[34]这里“罗寺”指称何物?姜伯勤先生曾就吐鲁番出土文书论述过家寺,他指出高昌麴氏王朝时期大量存在着家寺,如张寺、麴寺、索寺等,还有康寺以及史寺,进而说明康、史等姓已经跻身于当地大族之中,也说明康、史等姓人物数量可观,并有可能聚族而居。[35]根据以上分析,“罗寺”应为罗家寺,说明在当地大族中应有一席之地,也说明罗姓在当地大族中人物不少,而且可能有了聚落。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里的“罗寺”是本土罗氏的家寺呢,还是西域罗氏的?暂时无从考证;假如是西域罗氏家寺,那么此时西域罗氏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和势力了;但是假设毕竟不等于现实,一切真历史都需要充要的材料来佐证。
曾经活跃在西域的吐火罗人有以国为姓的习俗,或以吐火罗为姓,或以罗为姓。其记载在隋唐五代文献中不多,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却有少量明确记载吐火罗人的材料,这也许能帮助后人了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36]记载有吐火罗后裔的情况。本件是唐过所文书较长案卷之一,亦是吐鲁番所获十余件公验过所文书中仅见记载兴胡商队自西域往长安市易的文书,本案卷集中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上商队活动的情况。分为(四)段,第(一)段14行、第(二)段1l行、第(三)段8行、第(四)段25行,计58行1000字,为研究中外关系史所少见的史料。今只把与本文有关的第(一)段和第(四)段抄录如下:
本件文书涉及诸多人物,现将可能是西域裔民的姓名排列如下:康阿了(庭、伊百姓),史保(伊州百姓),曹不那遮(乌耆人),康师(高昌县人)、康尾义罗施、曹伏磨、可婢支、吐火罗拂延、突蜜、割逻吉、吐火罗磨色多、莫贺咄、何胡数刺、曹延那、康纥槎、康射鼻、康浮你了、曹野那、安莫延、阿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物,并非没有为胡人后裔的可能性,只是由于证据不足,实在归属难断,只好暂不分析。以上所列人物疑为西域裔民,理由如下:第一,从胡姓的角度来说。这里存在诸多九姓胡姓,如康、史、曹、何和安;也有吐火罗姓氏,如吐火罗(磨色多)、吐火罗(拂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有关吐火罗人及其裔民的记载在隋唐五代世存文献中廖若晨星,即便在多有可补传世史籍之缺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里也是屈指可数,所以这件文书涉及到吐火罗人后裔的记载,确实弥足珍贵;另外一些姓名,如可婢支、突蜜、割逻吉、莫贺咄、阿了,或者因为姓氏少见,或者释为姓氏缺载,但是无论如何把他们归为中国本土居民都是很勉强的。第二,从胡名的角度分析。上述历史人物的名字胡风色彩颇为严重,汉化程度不高。如(吐火罗)拂延,蔡鸿生先生认为“延”是胡名词尾,对于这一问题,在其著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此书还介绍了海外学者里夫什茨和高本汉先生的相应观点[40]。第三,在这件文书第二段有“兴生胡纥槎”的字样,似乎应指第(四)段中的“康纥槎”。如上文所述,兴生胡为西域商胡,尤指九姓胡,那么康纥槎应为西域胡人裔民无疑。这件文书中又称“但罗施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更加证明了这是一个从事中外贸易交往的胡人商队。姜伯勤先生在论述敦煌吐鲁番所见的粟特人时,把这一类西域胡人分为两类:著籍粟特人与未人籍粟特“商胡”[41]。尽管这件文书中所见的胡人裔民并非全部是粟特系统的,然而同样存在着这两种分类:著籍胡人与未著籍“商胡”,著籍者如保人庭、伊百姓康阿了、保人伊州百姓史保、保人乌耆人曹不那遮、保人高昌县史康师。综上所述,这件案卷反映了胡汉贸易的情况,涉及众多西域胡人后裔,笔者关注的重点还在于这件文书中的吐火罗后裔(吐火罗磨色多、吐火罗拂延)留存中国的状况。《新唐书》记载:“吐火罗,或日土豁罗,曰覩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42]吐火罗有以“吐火罗”或“罗”为姓的生活习惯,那么吐鲁番文书中是否有吐火罗后裔罗氏人物的材料,可能有,但是笔者无从看到,所以不敢断言;然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火罗后裔的材料可以让后人进行这种思考,这也为西域罗氏流寓中国再添可能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在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尽管有的罗氏人物只是可能为外来裔民;但是同时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笔者也深感资料的匮乏,因而无法进行更加深入和有意义的工作,比如说西域罗氏的源流,应该说从以上数则材料中实难做出正确的论断。
(二)敦煌出土文书所见西域罗氏
敦煌在隋唐五代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各族各色人等东来西往,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壮观局面,因而在敦煌出现胡人后裔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相比较,敦煌文书中有关西域罗氏的记载相对多了一些,其中一件有关敦煌从化乡的差科簿文书给人们提供了不少的史学信息。
P.3559+P.2657+P.3018+P.2803V《唐天宝年代(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是一件相当有价值的社会经济文书,提供了反映当时历史现实的不可多得的材料,特别是文书中含有的姓氏和名字的资料对分析西域胡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对于前人的学术史,如池田温先生所述,有石田干之助〈天宝十载丁籍所见敦煌地区的西域系统居民》,那波利贞《论正史记载的大唐天宝时代的户数与口数的关系》(3)(4),铃术俊《唐代丁中抽制研究》,曾我部静雄《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西村元佑《唐代敦煌差科簿研究——以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吐鲁番古文书为参考资料》以及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等[43]。其后,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差科簿及有关田制,徭役的文书,并结合史籍对文书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其中就包括差科簿文书;这是中国学者继《敦煌掇琐》和《敦煌资料》(第一辑)后对差科簿文书的又一次录文。厦门大学学者在《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中对此件差科簿文书做了录文及研究,卓有成效。
由于P.3559+P.2657+P.3018+P.2803V《唐天宝年代(750)燉煌郡燉煌县差科簿》特别是其中关于从化乡的资料对于分析西域罗氏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先把这件文书中的有关材料抄录如下:
1.二百五十七从化乡
2.一百一十七人破除
3.二十三人身死
5.罗虫子
8.三十五人逃走
9.罗拂那
Il.罗湿数延
12.罗数延
15.二十七人没落
16.罗勿沙
17.罗河诃
20.三人虚挂
21.罗磨娑
24.二十三人单身土镇兵
25.罗思明 罗铛娑
61.二十人下中户
78.罗伏帝延载六十二老男 上柱国
79.弟敬宗载五十三 上柱国 纳资
80.一百人下下户
96,罗阿铛载卌五 武骑尉
97.罗仙其载五十四 上轻车
106.罗宁宁芬载六十七 老男
107.男奉鸾载卅一 白丁 里正
114.罗鸟湿载廿二 中男侍丁
115.罗达数番载五十六 上柱国子
151.罗双流载卅二 白丁土镇
152.弟双利载廿 中男村正
153.罗特勤载卅五 白丁村正
154.弟顺盹栽卅 白丁土镇
155.弟宾宾载廿九 白丁土镇[44]
据统计:差科簿从化乡有姓名的居民共有236人,其中各个姓氏所占人数可列成下表:
表一
| 康氏 |
48人 |
安氏 |
39人 |
石氏 |
31 |
曹氏 |
30 |
| 罗氏 |
22人[45] |
何氏 |
20 |
米氏 |
10人 |
贺氏 |
7人 |
| 史氏 |
6人 |
裴氏 |
4人 |
辛氏 |
3人 |
唐氏 |
2人 |
| 张氏 |
2人 |
李氏 |
2人 |
王氏 |
2人 |
郭氏 |
1人 |
| 雷氏 |
1人 |
范氏 |
1人 |
黄氏 |
1人 |
翟氏 |
1人 |
| 索氏 |
1人 |
夫蒙氏 |
1人 |
|
|
|
|
在上述22姓中,康、安、石和曹四个姓所占人数最多,约占总人数的六成以上;罗、何、米、贺、史紧跟其后;这九姓共占总人数的九成以上,他们构成了从化乡居民的主体,这与其他各乡不同。差科簿其他乡里面所见的胡姓数目中,慈惠乡235人中有26人,悬泉乡79人中有25人,×乡88人中5人,寿昌218人中有6人,平均约占总数的一成以上。[46]
现在专注于从化乡的罗氏。罗氏在从化乡为第五大姓,仅次于康、安、石、曹诸姓,约占从化乡总人数的一成。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在从化乡有22人,但在慈惠乡、悬泉乡、×乡诸乡中却无1人(当然存在文书残缺的缘故),在其他乡中尚有康、安、曹、石、米、毕等胡姓,具体数字见前文,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根据上引文,从化乡被池田温氏定为唐朝沙州粟特人聚落。在这种典型的粟特人聚落中,罗氏大量出现而在其他乡中却无一人存在,罗氏俨然已经形成粟特聚落中的小聚落,试想若非罗氏不是胡人,怎能这样大量存现于胡人聚落中。前面已提到桑原骘藏氏,石田干之助氏、池田温氏、姜伯勤氏等都认同从化乡的罗氏为胡人。从而,基本上可以把从化乡罗氏定为聚居在粟特聚落中的胡人后裔。
下面再以罗氏为例说明胡名的问题。就胡姓的研究,桑原骘藏、向达、冯承钧、姚薇元诸位先生已经作出了不少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指出:“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47]所以,胡名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蔡鸿生先生在胡名研究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他指出国际学术界对粟特人名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有不少方法和成果可供我们借鉴和采择,尤其是穆格山粟特文书与敦煌、吐鲁番汉文文书中胡名的比勘,正在显示诱人的前景。[48]
根据池田温氏上引文,他把从化乡的名字分为胡式、汉式和归属难以确认的三组加以探讨。其分类标准是:把现代汉语仍实际使用的人名以及作为汉语人名在音韵乃至意义上都不感觉生硬的名字定为汉式;其他可以认定是汉语以外语言(伊兰“粟特”语、突厥语)的人名以及作为现代的汉语人名在音韵或者意义上使人感觉生硬的名字定为胡式;一个人名按照以上标准既可以定为汉式,又可以定为胡式,或者是归属于哪一类难于判断的人名,划人第三组。
根据池田温氏的分类,现在把罗氏居民的名字分类抄录如下,此为池田温氏据高本汉(B.KARLGREN)EtudeS.S.ur laP.honologie chinoiS.e(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并经平山久雄教示而做出的标准。胡式人名:(14人)
(罗)阿铛
(罗)阿了黑山
(罗)铛娑
(罗)达数番
(罗)特勤
(罗)伏帝延
(罗)拂(那)
(罗)磨娑
(罗)宁宁芬
(罗)湿数延
(罗)数延
(罗)顺沲
(罗)乌湿
(罗)勿沙
汉式人名:(4人)
(罗)奉鸾 (罗)敬宗
(罗)思明 (罗)虫子
归属难于断定的人名:(4人)
(罗)宾宾
(罗)双利
(罗)双流
(罗)仙其
由上列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从化乡22名罗氏人员中,胡式人名14人,三居其二,这说明这些西域罗氏尽管以汉族人的行为方式以国为姓,但是汉化程度不高,胡风尤其浓烈,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从化乡罗氏应为西域胡人后裔。
再来分析一下从化乡罗氏的胡名问题。根据蔡鸿生先生的论述[49],从语言学上解释一下胡名。蔡鸿生氏云,缀上- y'n,(阿维斯陀经以作yana -,yna -,古波斯语作yna -)和-P.m(米地亚语作famah -)的名字,与唐代译例进行比勘,这两个胡名词尾就是“延”和“芬”,是穆格山文书中最通行的粟特男名。在粟特语中,“延”字作“礼物”讲,兼有“荣典、庇佑”之义;“芬”字则是“荣幸、运气”之意[50],值得注意的是从化乡西域胡人后裔罗氏也有这样的粟特人名,如(罗)伏帝延、(罗)湿数延、(罗)宁宁芬、(罗)数延。由于笔者不通胡语,尚不知“湿数延”和“数延”的具体含义,只是根据蔡鸿生氏转述亨宁氏的论述,知道这几个胡名大概和“礼物”(“延”字的含义)有些关系吧,但实际上恐怕并非这样简单。另外“伏帝”(P.wt),为“佛陀”借入粟特语而来的,故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胡名“伏帝延”(P.wty’n)可释作“佛赐”或“佛佑”,含有佛教信仰的色彩,显示了宗教对胡名的影响‘51】。胡名“宁宁芬”( nnyP.m)则同样显示了宗教色彩,它内含“诺娜神”(nny)的名字[52]。“宁芬”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如唐代墓志中有关石崇俊的材料说“石崇俊祖讳宁芬”[53],根据这方墓志,石氏家族应为九姓胡人后裔。荣新江先生则认为“那宁”、“那你”、“宁宁”都是“Nanai“女神名字的不同音译,是娜娜女神信仰的反映[54]。荣新江氏在上引文中论证了粟特人早期存在娜娜女神信仰,罗氏以“宁宁芬”为名,表明罗氏亦信仰娜娜女神,不过这样的例子不多,近乎孤证,但也不能轻易否认罗氏存在这种信仰,如果罗氏真的存在娜娜女神信仰,那么罗氏与粟特人及其后裔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呢?在上述罗氏胡式人名中,还有(罗)特勤,据蔡鸿生先生论述,“特勤”取自突厥二十八等官号,即Tigin,这是粟特地区逐步突厥化,胡人取名吸收突厥成分的结果;又有学者解释“特勤”是突厥语tegin的译音,为酋长之义[55]。问题是同为西域胡人后裔的罗氏也突厥化,并取与粟特后裔相同的名字,西域罗氏与粟特系统究竟又为何种关系呢?
下面来分析一下罗氏的汉化问题。从年龄上分析,据上文,把罗氏人员列表如下:
从年龄上来看,六十岁以上胡式人名有两人,而汉式人名、归属难断者均无;五十岁至六十岁三类人数持平;四十岁至五十岁只有胡式人名一人;三十岁至四十岁,胡式人名居多;二十岁至三十岁,胡式人名少于其他。由此说明,基本是年龄越小,胡式人名所占比率越小。这与池田温氏在上引文中所归纳出的从化乡胡姓与年龄的关系一致,说明年龄与人名的胡、汉形式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表二
| 年龄 |
21~30 |
31~40 |
41~50 |
51~60 |
60~ |
| 胡式 |
1 |
2 |
1 |
1 |
2 |
| 汉式 |
|
1 |
|
1 |
|
| 归属难断 |
2 |
1 |
|
1 |
|
下面来分析一下具有亲属关系的几组罗氏人员:
表三
| 兄 |
弟 |
| 罗伏帝延(胡名) |
罗敬宗(汉名) |
| 罗特勤(胡名) |
罗顺陁(胡名) |
| |
罗宾宾(归属难断) |
| 罗双流(归属难断) |
罗双利(归属难断) |
表四
由上表中可知,在兄弟关系中兄多为胡式名,弟多为汉名或归属难断;在惟一一例父子关系中,父为胡名,子为汉名。由上述这种趋势,可以看出罗氏在逐渐汉化,这与从化乡其他胡姓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基本一致。
池田温上引文在论述居民的姓氏时提出的几个问题,依然应该引起注意。他说从化乡居民的胡姓与伊兰系统民族的固有姓名基本上没有关系,这是外来民族受汉人传统习俗的熏染,在汉化过程中有意识地采用了汉族的命名方式。罗氏人员采用汉族命名方式以“罗”为姓,就充分显示了其汉化进程。另外,池田温氏还指出了从化乡居民的各个构成姓氏中,每个姓氏人数的多寡,与该姓氏所在的国家的势力大小具有相应的比例关系。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化乡罗氏人数在从化乡姓氏中名列第五,仅次于康、安、石、曹四姓,充分显示了罗氏所在国家的势力强大。但罗氏所在国家究竟为何?是否就是池田温氏、姜伯勤氏等认为的吐火罗国呢?
如上所述,笔者从胡姓、胡名、胡人汉化等问题分析了唐朝天宝年代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的罗氏。根据以上分析,从化乡罗氏应为西域裔民。
还有一些敦煌文书显示了存在西域罗氏及其后裔的史学信息,这有利于人们了解西域罗氏的历史状况。
P.2629《年代不明(964?)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记载:“(前略)去三月十九日供于阗;罗尚书爱日洒王升(后略)”[56]这件文书显示了于阒罗氏后裔的存在,众所周知,于阗国素以尉迟为姓,但文书中显示的罗尚书是出身于阗国的呢,还是流寓于阗国的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于阗罗氏官居尚书一职。显示于阗罗氏存在的还有S.1366《年代不明(980 - 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前略)于阗罗阁梨身故助葬细供十分,胡[饼]五十杖,用麦四斗四升,油八合(后略)”[57]。阇梨指高僧,是较有身份的僧官大德。
这件文书不仅显示了于阒罗氏后裔的存在,而且这位于阗罗氏后裔是位高僧。以上两例流寓敦煌的于阗罗氏既有政界官员,亦有佛界高僧,表明西域罗氏在敦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P.3070《乾宁三年?(896?)行人转帖》记载了行人姓氏“龙藏破罗安张王赵阴薛唐邓令孤正等,安康石必罗白米史曹何,户户户,后齐程社桥屈韩吴高谈汜范禁龙高通”[58]。唐耕耦氏、陆宏基氏认为这段文字系蒙童所写,错误甚多,不能通读。[59]冯培红先生则对这段蒙童所写文字进行了考释,认为所列诸姓的三个部分中第一、三部分基本上是汉族姓氏,第二部分中“安康石必(毕)米史曹何”诸姓系粟特人,“罗白”亦为西域姓氏;同时他认为第二部分中的曹姓应当为粟特人,而非汉族曹氏;冯培红氏又从军队中蕃汉分隔编制来说明归义军时期粟特曹氏与汉族曹氏之间仍有界限。[60]冯培红氏上述推断有一定道理,其中一些论述也适用于罗氏。这件文书所列诸姓中第一部分中大部分是汉族姓氏,使得罗氏有为汉族罗氏的可能性;冯氏称第二部分中“罗白”为西域姓氏,白姓可能为龟兹姓氏,罗姓是否就被断定为吐火罗姓氏呢?那么罗姓为何又经常与粟特姓氏粘连于一起呢?这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颇有几例。这里姑且存疑,以后另行论述。另外军队中的蕃汉分隔编制,同时也说明了归义军时期西域罗氏与汉族罗氏之间存在界限。
在敦煌社邑文书中可以寻觅到一些西域罗氏的踪迹。S.2894《壬申年(972)十二月廿日社司转帖》有三件,是有关通知社员参加建福活动的。所通知的人中间有不少西域胡人后裔,其中第三件:
社司 转帖
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囗饼一双,净粟一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卅一日卯时
于罚(当为罗)家酒店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其帖速迪相
分付付,不得停滞。如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史启囗 康幸深 石海全 吉昆岗
罗瘦儿 曹达怛 白囗囗 米不勿
史幸丰 唐文通 宋苟奴 邦丑挞
泊知客 辛怀恩 何不勿[61]
陆庆夫氏根据社司转帖上所列人姓名中有史、康、石、曹、米及何诸姓,从而认为这些人为昭武九姓;并由罗为吐火罗姓,白为龟兹姓,进而得出此社成员大多数由西域胡人组成[62]。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仅仅据胡姓判断族属有些武断,而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胡人后裔不能等同于胡人,实际上上面的社邑文书体现的是胡人后裔聚居的生活情况。陆庆夫氏、郑炳林氏曾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的成员(社人)居住不会相距太远,体现了一个区域的居民特征。[63]所以,通过社邑文书可以了解聚落的情况。可以说这可能是一个有关胡人后裔聚落的文书,理由如下:首先,从胡姓上考虑,如陆庆夫氏上面指出的康、史、石、曹、米、何、白及罗诸姓皆为西域胡姓中所有,但这不足以说明有着这些姓氏的即为胡人或其后裔,然而毕竟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其次,从胡名上来了解,如(曹)达怛、(白)囗囗、(米)不勿及(何)不勿诸名尚留有浓厚的胡风色彩;至于其他存在胡姓可能的人物,如(罗)瘦儿、史启囗、康幸深、石海全和史幸半可以说具有汉式人名,假如他们确实为胡人后裔,则从姓名上来说,这些人已经汉化了;第三,从人数比例来分析,上述九人聚在一起占到总人数十五人的三分之二,倘若只有一两个具有胡姓的人在一起尚不易断定他们为胡人后裔,但是三居其二的人都存在为胡人后裔的可能性,所以也不便于把他们轻易视作汉人,倒是更增加了他们为胡人后裔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罗瘦儿。根据这件社邑文书,这15名社员参加建福活动的聚合地点为罗家酒店,据上文分析,这个社的成员大多数可能为西域胡人后裔,那么罗家酒店也很可能是胡人后裔所开的酒店,既然选择罗家酒店为聚会地点,那么西域罗氏在敦煌应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再来分析这件社邑文书,它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西域胡人后裔汉化的史学信息,以国(族)为氏,依照汉人生活习惯取姓;在一些胡姓人物中,已经开始取汉式名字为名,以致后人在没有其他历史资料的辅助下,已经不易判断其族属,只能进行最大程度的推测,这同时意味着存在错误的可能性;再者,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风俗活动,流行于民间,由中原传播到敦煌,进而影响到胡人后裔的生活习惯,使得他们同汉人一样参加社活动,这又是胡汉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吧;第四,S.2894《壬申年(972)十二月社司转帖》共3件,另两件是通知社员分别到曹家酒店、安家酒店参加建福活动聚齐的社邑文书。对于这几件文书(主要是有关曹家酒店的文书[64]),郑炳林氏、荣新江氏、冯培红氏皆有研究,认为社官和社长都是粟特姓氏,社人中也有明显是粟特后裔的情况,聚齐的地点为曹家酒店,这正是粟特人善于经营的商店,因而推测这是一个以粟特后裔为首的社。学者们从上述论述中也反证了笔者关于同一卷号中罗家酒店的推论。[65]
在敦煌社邑文书中还有一些可能为西域罗氏及其后裔者。P.3391《丁酉年正月社司转帖(稿)》缘春局席故“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廿日辰巳时,于灵图寺门前取齐”[66],所通知的社人中有罗佛利子、曹老宿、史文威及米员喜等。此件社邑文书中的上述几名社人都有胡姓,有的学者把他们定为粟特人,[67]其中“罗佛利子”不仅具有胡姓,而且名字亦应为胡名,胡风味道甚浓,此罗氏很可能为西域胡人后裔。S.1475 V2《申年五月廿一日社司转帖》中有“罗彦进”,[68]不知是否为西域罗氏,陆庆夫氏等人亦把他作为胡人(粟特人)看待。[69]在其他一些社邑文书中亦有罗氏,如P.3764V《年代不详(公元十世纪)十一月十五日社司转帖》中的“罗水官”,[70]还有P.3764V《年代不详(10世纪)十一月五日社司转帖》中的“罗水官”,[71]此二人应为一人,两件文书中还有其他同名复现的情况。另外有S.1475V3《申年五月社人壬奴子等牒》中的社人“罗彦进”,[72] S.1475VI - V2《申年五月赵庭琳牒及处分》中的“罗光进”。[73] S.5698《癸酉年三月十九日社户罗神奴乞求除名状》[74]是一件关于社户“罗神奴”及南“文英”、“义口”三人退社的文书,以上除“罗神奴”一家外,其余皆无法从姓名及文书内容判断罗氏人物是否为流寓敦煌的西域罗氏;只有“罗神奴”的名字尚存些许胡风,有可能为流寓敦煌的西域罗氏,但也不敢贸然确定,如胡适先生所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只有“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了。在另一件社邑文书中的罗氏有可能为西域罗氏或其后裔,即P.3073《庚寅年正月三日社司转帖》中的“罗僧正”,录文如下:
社司转帖
(前略)太子 翟僧正 曹僧正 安僧正 罗僧正 宋法律 戒随阇梨王 僧正
汜法律 马法律 王法律 杨法律 徐法律 阎押牙(衙) 吴押牙(衙) 阴押牙
(衙) 马押牙(衙) 高押牙(衙) 索草场 宋押牙(衙) 丑囗 阴押(衙)[75]
很明显,这是一个僧人社,就录文来看,以罗僧正为界,在罗氏之前(含罗氏)的“翟、”“曹”、“安”及“罗”多为胡姓所有,在罗氏之后诸姓大多为中原汉姓。如此鲜明的分界线,不能不引入注意和猜测,让人们更加怀疑罗僧正为流寓敦煌的西域罗氏,这一罗氏并且任职佛教界,这与前面提到的S.1366《年代不明[公元980 - 982年]归义军衙内麦油破用历》中的“于阗罗阇梨”相呼应,使人们易于相信存在流寓敦煌的西域罗氏或其后裔有在僧界任职的可能性甚至现实性。
还有两件文书中的罗氏有可能为西域胡人后裔。S.1898《归义军时期兵士装备簿》,今拣来其中具有胡姓的人物录文如下:
十将安祐成 押衙罗贤信 第四队副队押衙罗安住 押衙翟弘庆 兵马使 安文信
兵马使康通信[76]
上面列举有康姓一人,安姓两人,罗姓两人,翟姓一人,西域胡姓较为集中。其中,康通信在敦煌文书中多处出现,除这件文书以外,还有S.2228《亥年(843)六月修城夫丁使役簿》,P.4660《康通信邈真赞》等以及莫高窟第54窟中的供养人题记。[77]郑炳林氏据此推断康通信为粟特人(应为粟特人后裔,下同),进而认为康氏为归义军建立过程中功高厥伟的三个粟特人之一。[78]陆庆夫氏亦认为康通信为粟特人。[79]倘若历史事实如上面所说,那么押衙罗贤信,副队押衙罗安住与粟特人后裔兵马使康通信在同一件文书中出现,并且同在归义军府衙中任职,从而人们有理由认为两位罗氏人物很可能是流寓敦煌的西域胡人后裔。倘若如此,那么兵马使罗恒恒亦为西域罗氏。P.3458《辛丑年(941 7)押衙罗贤信贷绢契》中有:
(前略)
贷绢人押衙罗贤信(押)
囗承弟兵马使罗恒恒(押)
见人兵马使何
(后略)[80]
显而易见,如果罗贤信为西域罗氏,那么罗恒恒亦为胡人后裔,另外此文书中还有西域胡姓“何”姓,也为推测罗氏为胡姓罗氏增加了可能性。
前文笔者讨论了敦煌文书中涉及西域罗氏及其后裔的材料,除此之外,在敦煌文书里面还有一类罗氏——罗盈达一族,他们在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身居要职,官高位显,在归义军府衙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分析西域罗氏流寓中国这一问题时,对于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罗盈达一族,有必要对他们的家族源流作一分析,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们究竟是中原罗氏还是胡人后裔呢?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下面先把罗盈达一族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罗盈达的资料主要见于P.2482、S.3405、P.3785、P.2916等几件敦煌文书,其中以P.2482《罗盈达邈真赞并序》[81]和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82]最为详细。罗盈达,生年不详,卒于943年,唐末五代沙州人,字胜迁;后唐同光元年(923)官职节度押衙,后以战功升为将头;不久又因为能够训齐士卒,部领军机,擢升为马步军都知兵马使,后于长兴四年(933)任职紫亭镇使,官至河西应管内外诸司马步军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使大夫;后罗盈达统率军队,于曹元德时,讨伐甘州回鹘。罗文达,罗盈达的次兄,归义军节度押衙,P.2482、P.4640有记载。罗文通,罗盈达的三兄,归义军节院使,P.2482有提及,但其生平事迹敦煌文书缺载。罗进通,罗盈达的四兄,御史中丞,P.2482有提及,其生平事迹敦煌文书也缺载。罗通信,罗盈达的五兄,蕃部落使,P.2482有提及,其生平事迹敦煌文书缺载。罗通顺,罗盈达的弟弟,为宁州刺史检校司空御使大夫,P.2482有提及,其生平事迹敦煌文书也缺载。下面看一下罗通达的情况,P.3633、P.4640、S.4654等敦煌文书有记载,其中以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83]最为详细,罗通达是罗盈达的堂兄,为唐末五代敦煌人,累至归义军节度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阵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使大夫、上柱国;罗通达与宋惠信、罗进达等同有拓疆守土之功;天佑三年(906),在伊州回鹘犯境时,[84]力战获胜;后于阗路阻,乃率兵收复两城,返取伊吾;后梁开平间出使吐蕃,欲借兵以抗回鹘,援兵未至,回鹘可汗遣狄银统兵围沙州,金山国遂派宰相及大德僧人求和,尊回鹘可汗为“父”,自称为“子”。罗进达为御使,亦对归义军政权有功,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有提及,其生平事迹不详。罗元定,罗盈达之子,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有提及,但其生平事迹不详。
根据上文可知,罗盈达一族在唐五代敦煌归义军府衙里面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不凡的作用。回归“西域罗氏”这一主题,这一罗氏的家族渊源是什么呢?我怀疑罗盈达一族存在为胡人后裔的可能性,理由如下:
首先,从任职情况和婚姻关系来看。归义军政权是蕃汉联合政权;冯培红先生进一步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应以粟特人为主并联合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85]同时,荣新江先生从另外的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确认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一族为粟特胡人后裔。[86]如前文所述,罗姓在西域胡姓中存在,那么罗盈达一族是否为“番汉政权”中的胡人后裔呢?让我们先从他们的任职情况来看一下。罗盈达任都指挥使,堂兄罗通达任衙前都押衙兼内外排阵使,兄罗文达任节度押衙,兄罗文通任节院军使,兄罗进达为御使,兄罗通信任蕃部落使等。罗盈达的官职升迁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完成的,在后唐同光元年(923)任职节度押衙,后升为将头,不久又升为马步军都知兵马使,于长兴四年(933)任职紫亭镇使,官至河西应管内外诸司马步军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使大夫。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罗盈达任职都指挥使一事。冯培红氏称:“都指挥使、指挥使在五代宋世史籍中最为常见,是藩镇使府或宋代中央禁军中的显职军将……五代之际,都指挥使逐渐取代都知兵马使,成为曹氏归义军政权中的重要军职,总领军务,权职与原都知兵马使基本相同。”[87]都指挥使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府衙中的最高统军将帅,官高位显,见诸文书中的有三位:曹仁裕(曹良才)、罗盈达、曹贤顺。曹仁裕(曹良才)的资料见于S.8683《曹仁裕等算会牒》、S.8665《供物牒》等文书,他是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长兄;而曹贤顺是节度使曹宗寿的儿子,他就是由“检校兵部尚书衙内都指挥使”一职升为曹氏归义军历史上最后一任节度使的,可见两位曹氏人物都非比寻常。在都指挥使这样重要的职位上,位高权倾,位列其职的肯定是与曹议金一族有重大关联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见诸文书的三位都指挥使中的两位都是曹氏人物,而且都是曹议金的本家,惟独罗盈达一人不是曹氏人物,此罗氏凭什么显赫的资本官居高位呢?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根据荣新江氏、冯培红氏的论断,敦煌曹议金一族应为粟特人后裔,那么曹仁裕、曹贤顺都是流寓中国的胡人后裔了。在都指挥使这样重要的职位上,既然三居其二都是胡人后裔,那么如果罗盈达是西域胡人后裔,不是更加合情合理吗?如果仅仅因为罗盈达一人官居高位就这样下结论显然过于武断,关键是罗氏一族多人在归义军府衙里面身居要职,如上所述,有堂兄罗通达,兄罗文达,兄罗文通,兄罗进达,兄罗通信等。但是极为可惜的是上述多人材料文献缺载或者语焉不详,只有罗通达的材料比较完备。
下面再来看一下罗通达的任职情况。罗通达累至归义军节度衙前都押衙,充内外排阵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使大夫、上柱国。在这里应该对于罗通达任职“都押衙”一事进行关注。冯培红氏称:“都押衙、押衙是唐五代藩镇使府中的重要军将,为节度使的亲信,职级高,权位重,最为节度使倚重。都押衙、押衙构成了归义军政权的中间支柱,他们出自使府衙内,掌握内外实权”,又说:“归义军押衙官职体系,以都押衙地位最尊,职权最重,都押衙分左、右两厢,各统两厢的押衙”[88]。由见可见,都押衙是归义军押衙官职体系中首屈一指的重要职位,其任职者为节度使所倚重。罗通达官居都押衙一职,在归义军府衙中的地位非比寻常。另外,罗通达不仅官居都押衙一职,更兼内外排阵使。“内外排阵使”在敦煌文书中仅仅在这里出现一次,应为当时罗通达训练军队的军职。[89]可见,罗通达在归义军政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上,罗盈达一族官居要职,而且是族人为官者人数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与他们可能的胡人后裔身份有关呢?
上面笔者从罗氏人员的任职情况讨论了他们的源流,下面再来看一下婚姻关系。罗盈达的夫人为曹氏,是曹大王曹议金的至亲妹妹,所以罗盈达一族与曹议金一族有着重要的姻亲关系,现在曹议金一族已经被论定为胡人后裔,那么从胡人内部通婚的情况来看,[90]是否可以把罗盈达推测为胡人后裔呢?
综上所述,从任职情况和婚姻关系两个方面来看,罗盈达一族确实存在着为胡人后裔的可能性。
其次,疑有“冒称郡姓”的可能。
罗盈达家族源流何处?P.2482《罗盈达邈真赞并序》和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称之为“豫章郡罗府君”,后一文献还详细写明了其家族渊源“其先著姓,本自颛顼末胤,受封于房州罗国,故号罗氏。后一子任职敦煌,子孙因官,遂为此郡人也”;在另外一件敦煌资料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中称罗通达为“豫章罗公”。这些就是可以见到的表明罗盈达一族源流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似乎很明确了,罗盈达一族就是豫章罗氏;但是笔者对这些文献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因为除了这几处写明“豫章罗氏”以外,在敦煌文献中再无其他材料佐证罗盈达一族为“豫章罗氏”,亦无另外的豫章罗氏人物;同时在其他传世史乘和出土文献中,也见不到P.2482《罗盈达墓志铭并序》所云的罗氏迁徙敦煌的记载,难道这些不让人们对罗盈达一族的源流表示怀疑吗?罗盈达一族称之为“豫章罗氏”,极有可能是冒称郡望。
在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冒称郡望的事情并不罕见,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一族即为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曹议金一族本为粟特胡人后裔,他们为了抬高自身的门望,积极追求门第,便于有效的控制敦煌地区。因为中原郡望有较强的说服力,所以曹议金一族就以“谯郡曹氏”当作自己的郡望。[91]罗盈达一族多人在归义军政权内任职,如果他们没有显贵的门第,就失去了升迁的一个重要资本,所以罗盈达一族有冒称郡望的必要性;另外,从罗曹联姻来看,与冒称为“谯郡曹氏”的曹议金的贵妹联姻,门当户对是需要考虑的,那么“豫章罗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依托,因为“豫章罗氏”是名门望族,在隋唐五代的历史中,豫章罗氏颇有些著名的人物,如任职魏博节度使的罗弘信一族,[92]其先就是豫章罗氏。所以,笔者认为罗盈达一族存在冒称“豫章罗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如果罗氏一族不是豫章罗氏,又是哪支罗氏呢?由于材料所限,只好采取排除法。根据前文所述,可以知道罗氏有豫章、齐郡、襄阳、河东、蜀郡、胡人叱罗氏改称罗氏、西域罗氏等几支。在敦煌文献中从未见到中原齐郡、襄阳、河东、蜀郡罗氏以及胡人叱罗氏改称罗氏的记载,看来可以确定罗盈达一族族源不是这几支罗氏;那么剩下的只有西域罗氏这一种情况了。况且如前文所述,西域罗氏确实曾在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特别是敦煌,在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西域罗氏的踪迹;事实上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93]它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前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其在中外交往中不凡的作用和地位,所以不难解释敦煌经常会出现各族各色人等东来西往,络绎不绝的情况,故而也遗留了异族在敦煌流寓的史迹,所以在敦煌出现胡人后裔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因此笔者有理由怀疑罗盈达一族为流寓敦煌的西域罗氏后裔。
综上所述,在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中,官居要职的罗盈达一族疑为胡人后裔。但是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材料的原因以及笔者学养有限,并未发现能够直接证明罗盈达一族为胡人后裔的材料,因而笔者的结论是审慎的,在行文中用的是“怀疑”、“可能”等不确定字眼,希望有新材料的出现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由上可知,敦煌文书中存在有关西域罗氏存现中国的记载,其中有关敦煌从化乡的差科簿文书最为珍贵,给人们提供了不少罗氏尤其是处于中下阶层罗氏的历史资料,让后人从不同方面对之进行采择分析;但遗憾的是从目前所见的材料中依然不易鉴定敦煌出土文书中西域罗氏具体来自何方,让后人仍然处于迷惑之中。
(三)隋唐五代出土墓志所见西域罗氏
在隋唐五代出土墓志中可以见到西域罗氏的活动材料,这种除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外的又一类出土文献给人们增添了一些了解西域罗氏流寓中国的情况。下面把一些重要墓志排列如下并进行解释。
材料一:
大唐故陪戎副尉罗府君(甑生)墓志铭并序
公讳甑生,阴山人也。昔贾谊腾声,不阶七命之重;终军诞秀,岂竟六极之先。虽名擅国华,地殊人望。尚延悲于当代,永贻恨于终古,矧夫家承阀阅,代茂簪袨。松柏成行,芝兰克嗣。存诸图谍,讵烦覙缕。祖日光,囗任秦州都督,谥日盘和公。山川通气,珪璧凝姿。天优其才,人济其美。滔滔不测,若江海之纳川流;严严高峙,若山岳之囗厚地。父季乐,隋鹰扬郎将。竹符花绶,绛节碉舆。宠冠百城,威隆四镇。公囗胄清华,囗庭礼让。天经地义,温清叶于无方;共寝同蔬,邕穆施于有政。情忘囗辱,志逸江湖。纵偃止文场,栖迟笔海。浮云名利,不从羁囗之劳;囗囗林亭,自得逍遥之致。起家秦王左右陪戎副尉囗囗囗囗于丹囗镜知止于青编。脱落微班,优游衡泌。悲夫!四游挥忽,千囗倏。香号返魂,居然莫致。药称不死,竟是空言。显庆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终囗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夫人康氏,幼贻门范,得规矩于自然;夙囗囗囗,囗婉顺于天性。贞襟霜净,秀质霞开。何言逝水沦波,悲泉落华。囗恒娥之窃药,攀月桂而忘归。类弄玉之登仙,奏风箫而永去。以仪囗二年二月终于章善里宅,春秋六十有九,以调露元年十月廿三日,合葬于河南界北邙之礼也。子神苻等,茹荼衔恤卫囗,援柏凝哀。恐天长地久,邈矣攸哉。式镌贞琬,光昭夜台。其词日:业延家庆,门彩孕庭,代称领袖,门擅簪袨。陶甄地义,隐括天伦。逸韵飙囗竖,清晖日新。其一,天地不仁,神心多忍。四序宁借,百龄囗尽。愚智同城,彭殇齐轸。讵偶大椿,吾从朝茵。其二,猗欤淑媛,契合丝缗。展敬苹囗藻,施工组纠。德彼九族,恩沾六姻。操凌竹柏,润叶瑶珉。其三,眇眇造化,茫囗区域。短景易穷,浮生有极。夜川不囗,朝霞谁食?洛浦云销,巫山雨息。其四,沉晖不驻,阅水徒惊。空余乡像,非复生平。霜飞幽坠,月照空茔。式镌贞琬,方传颂声。其五。洛州偃师县人也。[94]
对于这方罗甑生的墓志,荣新江、刘铭恕两位先生皆有论述。荣新江氏在《北朝隋唐栗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论述凉州(今甘肃武威)为胡人聚落集中地区时曾经引用《罗甑生墓志》:“祖日光,囗任秦州都督,谥日盘和公”,并认为盘和即盘禾,为凉州属县,或许罗氏先人曾在此居住,所以才被谥为盘和公。[95]从而认为罗甑生一族可能为胡人后裔。刘铭恕氏则在《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中就罗甑生的氏族、祖籍、祖辈的仕宦及其本人的出身,并其配偶的氏族诸方面考之认为罗氏应为吐火罗人。[96]
结合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就罗甑生墓志笔者申而论之。第一,罗甑生及夫人康氏生年考。墓志中云(罗甑生)于“显庆四年(659)十二月十三日,终囗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引文中缺字应为“于”字。据上,罗甑生生年应为隋开皇十五年(595),为隋、初唐时期的人物。罗甑生夫人康氏“以仪口二年二月终于章善里宅,春秋六十有九”。引文中缺字当为“凤”字。据上,夫人康氏生年当为隋大业四年( 608)亦为隋、初唐时期的人物。刘铭恕氏云罗氏卒于调露元年(679),康氏卒于显庆四年(659),显然与墓志不符,皆误。据墓志,罗甑生及夫人康氏于调露元年(679)十月廿三日.合葬于河南界北邙之礼。第二,就种族籍贯而言,罗甑生墓志云罗氏为阴山人,查阅《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太平寰宇记》、《通志》、《古今图书集成》等涉及姓氏的传世文献以及敦煌文书,如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北8418《姓氏录》等出土文献,不见中原罗氏有郡望为阴山的一支,由于华夷观念的存在,中原罗氏不大可能称自已为阴山人,由此,推断阴山人罗甑生一族极有可能为胡人后裔;另外胡人后裔能承认自已为阴山人的也不多见,因为他们汉化过程中,极力遮掩自身的族属、籍贯,不仅以汉人的生活习惯取姓名,而且不断有冒称郡望的事情发生,对此学者们多有论述。[97]第三,由胡姓来看。罗甑生夫人为康氏,康姓在西域胡姓中存在,康居,康国都“以国为氏”,胡人后裔罗氏娶同为胡人后裔的康氏为妻,这在胡人系统内部颇为常见。[98]由上分析疑康氏亦为胡人后裔。第四,从胡名来说。罗甑生祖日光,“日光”二字有胡风色彩,隐约含有一种对光明的信仰,由于证据不足,这只能是一种推测;罗甑生有子名神符,刘铭恕氏认为“神符”一称,亦偶见于少数民族中,如唐太常乐工,即有名的裴神符为疏勒人,[99由此看来“神符”之名确实存在于胡人名字中,这也把这方墓志中的罗氏定为胡人后裔增添了一个证据。第五,罗甑生祖孙四代人都已汉化,其汉化表现为罗氏一族在北朝隋唐任职(罗日光可能在北朝任秦州都督),死后有谥号等。即使认定他们为胡人血统,也只能称作“胡人后裔”。刘铭恕氏把罗氏一族定为吐火罗人,这里暂不讨论其出身国别;即使出身为吐火罗国,由于他已经汉化,入华日久,也只能称为吐火罗人后裔,这样才符合历史,具有历史感。第六,关于“谥日盘和公”.盘和即盘禾,为凉州属地,荣新江先生认为或许罗氏先人曾经在此居住才被封谥号为盘和公的;[100]因为凉州为胡人聚落集中之所在,根据荣新江氏的推测,既然罗甑生的先人可能在凉州居住,又因为罗姓在入华姓氏中也存在,那么就存在罗氏具有胡人血统的可能性。
材料二:
大唐故翊卫大督罗府(端)墓志铭并序
君讳端,字文静,洛州洛阳人也……祖业,周司隶从事……父穆,隋并州太原县令……
君……以隋大业十一囗授朝散大夫。……囗贞观五年,授左翊卫大督……以大唐麟德元年
十月六日,告终私室,春秋七十九。即以其年岁次甲子十一月乙巳朔五日已酉,与夫人杨
氏合葬于邙山之原礼也……有子道祐等……其铭曰:绵绵远系,昭昭清绪,族茂江皋,声
芳汝豫……[101]
上面这方罗端罗文静墓志引文中三处残字依次应补入“年”、“以”、“显”或“闻”字;据志文,这方墓志的题目“翊卫大督”前脱一“左”字。
墓志云,罗端罗文静“以大唐麟德元年十月六日告终私室,春秋七十九”,那么罗氏应当生于开皇五年(585),为隋、初唐时期的人物。据墓志,罗端罗文静为洛州洛阳人。根据传世史乘以及出土文献,并未见罗氏郡望为洛州一说。岑仲勉先生据《元和姓纂》云罗氏有齐郡,襄阳、河东三族,代北氏族叱罗氏改为罗氏,其上必冠以“河南”字[102]。显然“洛州洛阳人罗文静”,非“齐郡、襄阳、河东三族”等中原罗氏,同时并未冠以“河南”字,想必也非代北氏族叱罗氏,他是否是西域罗氏后裔?虽然证据不足,但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推测。洛阳作为唐朝两京之一,地位尤其重要,是唐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重镇,更有诸多学者认为洛阳为丝绸之路的起点,[103]西域人后裔冒称洛阳人氏,籍以抬高门第,这是可以理解的。铭文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绵绵远系,昭昭清绪,族茂江皋,声芳汝豫”,江皋为江边的高地,汝豫为河南地方,这名话说罗端一族源远流长,并试图与长江、河南的罗氏郡望拉上关系。刚才已经分析过,罗端一族似乎与河南不易发生关系;在姓氏书中所列几支中原罗氏中,能与长江扯上边的,只有襄阳罗氏,襄阳罗氏是大族,倘若罗端一族真与襄阳罗氏有关系,这种堂而皇之的事情何需隐晦而改称洛州洛阳人呢?恐怕罗端一族也难与襄阳罗氏有关联。这也增加了罗端一族非中原罗氏的可能。
资料三:
大唐故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石氏,讳崇俊,字孝德,其盛族徽烈,家谍著焉。府君以曾……[104]奉使,至自西
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皇考讳思景,泾州阳府
左果毅。洎府君为传家之庆……素囗宦情。(府居)有子曰日清……授左威卫左司戈,掌
剑南道泉谷之任……(府君)不幸遭疾,以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享
年八十有一。夫人洛阳罗氏,温淑闲茂,礼法克修,昼哭声悲,素帷心苦……[105]
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提到这方墓志,并认为石崇俊是西域人,在流寓以及卒于长安之西域石国人墓志中,石崇俊一石为最初之发见,弥足珍贵[106]。
此墓志系长安出土。根据这方墓志,石崇俊生于开元四年(716)卒于贞元十三年(797),为唐朝中期历史人物。由材料提供的历史信息,如“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于秦,今为张掖郡人也。祖讳宁芬,本国大首领散将军”,可以判断石崇俊一族为西域人氏,具体应为昭武九姓胡人(石国人)及其后裔。后流寓张掖、长安等地。石崇俊祖石宁芬的名字,多见于胡名,韦伯,里夫什茨,蔡鸿生、荣新江等中外学者多有论述[107]。石崇俊一族显示了胡人汉化的现象,仅从名字可见端倪,祖“宁芬”,父“思景”、本人“崇俊”,字“孝德”,子“清”,一目了然,勿庸赘言。由此可见,石崇俊一族为西域人应无疑义。因为笔者文章的着重点在于西域罗氏,所以上述材料中的“洛阳罗氏”就成了关键之处了。石崇俊夫人罗氏是否源出西域罗氏呢?现在尚无充要的材料来证明,然而在人华粟特人的婚姻形态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在很长的时间里,粟特人中间保持着内部通婚的习惯,陈海涛先生认为安史之乱以前,人华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同时与其他人华少数民族通婚也较普遍,而与汉人通婚则较少见,对此荣新江先生表示认同。[108]从唐朝时期人们的结婚年龄推断,已经汉化的石崇俊应在安史之乱前完成终身大事的。根据陈海涛先生的观点,人华栗特人石崇俊与“西域罗氏”结亲可能性较大,而与“中原罗氏”嫁娶的可能性较小。另外石崇俊夫人被称为“洛阳罗氏”值得怀疑,笔者在分析《罗甑生墓志》的时候作过同类分析,根据传世史乘以及敦煌文献中姓氏书的相关记载,均不见罗氏郡望为洛阳的一支;而入华外族人士冒称郡望,把籍贯定在两京(长安,洛阳)者,却比比皆是,唐代墓志多见此事。所以由以上诸点,笔者有理由怀疑石国人后裔石崇俊夫人罗氏为西域罗氏后裔。
综上所述,现存的隋唐五代墓志中存现西域罗氏及其后裔的少量材料,但是把他们确定为西域罗氏及其后裔还仅仅是怀疑,资料并不是十分充分。
(四)隋唐五代传世史乘所见西域罗氏
隋唐五代的传世史乘不可谓不多,但是有关西域罗氏的材料的确是少之又少,笔者翻检了几十种隋唐五代的基本史料和主要史料,却也只是在《册府元龟》以及正史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有关西域罗氏的资料,下面就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
1.《册府元龟》所见西域罗氏
《册府元龟》卷971“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吐火罗国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囗来献方物。”[109]
《册府元龟》卷975“开元二十六年(738)二月癸丑,吐火罗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囗来献方物,授果毅,赐绯袍,银带,鱼袋及帛三十匹,放还蕃。”[110]
这两条材料叙述的时间同为开元二十六年(738),都是有关吐火罗人罗底囗来大唐献方物,可谓唐朝与吐火罗关系史中不可多得的材料。西域诸国以国(族)为姓的材料在文献中数见不鲜,如西域康、安、曹、石、米、何、穆、毕、支、车、鄯等氏分别为康国或康居,安国或安息,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穆国、毕国、月氏、车师、鄯善等国(族)人或其后裔;当然也有不以国为姓者,如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等。吐火罗人有以国为姓者,云吐火罗氏、罗氏;亦有不以国为姓者,如安延师[112]、乌利多(乌那多)[113]、仆罗[114]等。从以上两则有关吐火罗与唐朝贡使关系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开元年间吐火罗与唐朝的交往情况,这与开元盛世,四夷宾服的历史大背景相印证,加大了材料的可信性;而且给后人提供了吐火罗入存在以国为姓的史实,罗底口即为一例。
据记载,《册府元龟》中有反映吐火罗周边的西域国家和唐朝之间的贡使关系的材料。
《册府元龟》卷975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十月甲寅,护蜜国王罗真檀来朝,献方物。赐帛兼袍银钿带,留宿卫。”[115]
《册府元龟》卷975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九月丙子,护蜜国真檀来朝,宴于内殿。授左金吾卫将军员外,赐紫袍带、鱼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还蕃。”[116]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可知,真檀应为罗真檀。下面亦同。
《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记载:“天宝八载(749)八月乙亥,护蜜国王罗真檀来朝,请宿卫,授左武卫将军,留宿卫。”[117]
关于护蜜国王罗真檀,《全唐文》亦有记载。《全唐文》卷二八七有《敕护蜜国王书》:“敕护蜜国王真檀……”;又有《敕识匿国王书》:“敕识匿国王乌讷没莫贺咄:卿比与护蜜相为唇齿,而发匐凶狡,劫杀商胡,罪不容诛,走投异域。朕知其恶积,改立真檀,遽闻却来,还占本国……”[118]
《册府元龟》卷964:“开元八年(720)三月封护蜜国王罗施伊具骨咄禄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为护蜜王,赐紫袍金带七事,并杂彩五十匹。”[119]
《册府元龟》卷971:“肃宗至德三年(758)正月,护蜜国王使大首颌罗友文来朝。”[120]
《册府元龟》卷976:“乾元元年(758)二月乙卯,护蜜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来朝。加特进左武卫大将军。仍听还蕃。”[121]
《册府元龟》卷971:“天宝九载(750)正月,骨咄国王罗全节遣大首领鹘汗达干来朝,献口四十三,胡马三十匹。”[122]
《册府元龟》卷965:“天宝十一载(752)正月壬寅,册骨咄国王罗全节为叶护。册日:“维天宝十一载,岁次壬辰(原作寅误),正月已卯,二十四日壬寅(原作辰误)皇帝诏日:于戏!畴赏懋功,无隔于中外。怀荒恤远,谅归于典谟。咨尔骨咄国王罗全节,夙遵声教,志尚忠节。作捍边疆,勤效斯著。顷者以群丑拨动,方欲胁从,而忠恳不渝,始终弥固。言念于此,嘉尚良深。是用授予骠骑大将军,仍册为都护。尔其祗膺典礼,慎守边疆,贻庆子孙,受兹宠锡。可不美欤?”[123]册文亦见《全唐文》卷三十九[124]。
《册元府龟》卷975:“天宝二年(743)二月乙丑,解苏国阿德悉遣大首领车鼻施达干罗顿毅等二十人来朝,且献方物,名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放还蕃。”[125]
《册府元龟》还记载吐火罗与唐朝交往的另外一些材料,因上面没有显示罗氏人物,兹不赘言。
上述《册府元龟》及《全唐文》中的资料显示了西域罗氏曾经流寓中国的情况,这些罗氏人物共计有:吐火罗国大首领罗底口、护蜜国王罗真檀、护蜜国王罗施伊具骨咄禄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护蜜国大首领罗友文、骨咄国王罗全节、解苏国大首领罗顿毅。上述西域诸国皆有以“罗”为姓的情况,如果把吐火罗国的罗氏解释为“以国为姓”,同时护蜜、骨咄、解苏诸国也存在罗氏,那么这些西域国家与吐火罗国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池田温氏以“吐火罗势力圈”以概之,并推断唐朝敦煌从化乡罗姓当与吐火罗有关联。[126]
2.隋唐五代正史所见西域罗氏
笔者检阅隋唐五代的正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发现了一些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下面把这些材料举列如下,并加以分析。
《新唐书》记载:“章求拔国,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种。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附之。地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人,无城郭,好钞暴,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其王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职贡不绝。”[127]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本为西羌种的章求拔国(章揭拔)的王叫做“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他为西羌种,可以说是西域罗氏。章求拔国(章揭拔)的地理状况是这样的,它位于悉立西南的四山中,与东天竺接壤,应该为中天竺国的属地,当然属于西域无疑。材料中还提到章求拔国(章揭拔)的王遣使入朝、助唐讨伐,并且职贡不绝,说明这一国家与唐王朝有着一定的联系,以致于在正史中有迹可寻。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章求拔国(章揭拔)的国王为西域罗氏,那么民众中也应该有罗氏人物;所以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的材料为后人寻访西域罗氏在中国的存现情况作了有利的说明。
《新唐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西域罗氏:“护蜜者,或日达摩悉铁帝,日镬侃,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赢,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迦审城,北临乌浒河。地寒冱,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麦,宜木果,出善马。人碧瞳。显庆时以地为鸟飞州,王沙钵罗颉利发为刺史。地当四镇人吐火罗道,故役属吐蕃。开元八年,册其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十六年,与米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明年,大酋乌鹘达干复朝。王死,册其从弟护真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颉吉匐请绝吐蕃,赐铁券。八载,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乾元元年,王纥设伊俱鼻施来朝,赐氏李。”[128]
这段材料提到护蜜国的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129]。护蜜(达摩悉铁帝、镬侃),元魏时叫做钵和,是吐火罗的故地,所以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应该是吐火罗势力圈的西域罗氏。开元八年,唐朝册封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为王。材料中还提到开元十六年(728),护蜜王西域罗氏与昭武九姓胡人米国首领米忽汗同献方物的事情,说明吐火罗势力圈的西域罗氏与九姓胡人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护蜜国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尔死后,其从弟(罗)护真檀[130]接替王位,这说明西域罗氏在护蜜国,在吐火罗势力圈都有一定的影响。(罗)护真檀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入朝,宴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八年(749),(罗)真檀来朝,请宿卫,诏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后来(罗)真檀又遣首领朝贡,这些记载同时在《册府元龟》和《全唐文》中有迹可寻。[131]根据以上材料,可以发现护蜜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密切,以致于被赐以国姓“李”。从以上材料能够看出西域罗氏在吐火罗势力圈有一定影响,并且能够了解和唐王朝的贡使情形。
《旧唐书》中有关于罗劭权的材料:“(罗让)子劭京,字子峻,进士擢第,又登科。让再从弟咏。咏子劭权,字昭衡,进士擢第。劭京、劭权知名于时,并历清贯。”[132]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罗劭权为番相[133],但并没有申而论之。
综上所述,尽管材料有限,但是在隋唐五代的正史中确实存在着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为我们探求西域罗氏的渊源提供了更多的帮助。
四、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浅析
一、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生产生活状况
在前面,笔者对于隋唐五代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指出了为或者疑为西域罗氏及其后裔的历史人物;今就笔者前文所引传世史乘及出土文献,把西域罗氏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简要的分析,下面我主要从职业分布、社会阶层、以及婚姻关系等情况排比分类并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职业分布
如果我们想了解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的生产生活状况,那么就有必要对罗氏人物的职业状况进行一番分析。由于有关材料多数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无系统性可言,所以很难对罗氏人物的职业状况作出客观、细致的分析,但是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尽量把其中几个典型的职业进行如下分析:
1.从事商贸活动
A.开酒店。s.2894《壬申年(972)十二月廿二日社司转帖》有三件,据社司转帖内容,众社员分别聚集到罗家酒店、曹家酒店、安家酒店参加有关活动,其中写道,“右缘常年建福一日,人各口饼一双,净粟一斗,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卅一日卯时于罚(笔者注:当为罗)家酒店取齐,(后略)”并于社人名单中写有“罗瘦儿”。134由此可见,敦煌的罗氏从事商业活动,开罗家酒店,而且此酒店成为人们活动的聚齐地点。
B.进行贸易活动。
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中的“兴胡罗世那”以及同一墓葬出土的《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中的高昌县“罗易没”都是作为保人出现的,一个是未著籍者,一个是著籍者,两人各参与了一件贸易活动,(买马事件、买婢事件);更兼罗世那前有“兴胡”二字,更加确认了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有进行贸易活动的人物。
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有吐火罗后裔(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参加了兴胡商队自西域往长安市易的情况,详细论述见笔者论文的其他部分及程喜霖先生的《唐代过所研究》[135]。
2.任职官场
罗氏人物在官场内遍布上中下各个阶层,分布较广。其中既有在中上阶层身居要职的人物,如吐火罗势力圈的诸多来华史臣(罗真檀、罗友文、罗顿毅、罗全节、罗底口)以及其他文献记载中的番相罗邵权、大唐陪戎副尉罗府君(甑生)、大唐翊卫大督罗端罗文静等等,又如疑为胡人后裔的敦煌归义军时期的罗盈达一族,官职显要,罗盈达任都指挥使,堂兄罗通达任衙前都押衙兼内外排阵使,兄罗文达任节度押衙,兄罗文通任节院军使,兄罗进达为御使,兄罗通信任蕃部落使;又有处于下层的低级官兵,比如P.3764V《年代不详(公元十世纪)十一月十五日社司转帖》中的“罗水官”和P.3764V《年代不详(公元十世纪)十一月五日社司转帖》中的“罗水官”,以及P.3559+P.2657+P.3018+P.2803V《唐天宝年代(750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中的武骑尉罗阿铛和土镇兵罗思明.
由上可见,任职官场的罗氏人物分布层面较广,遍布各个阶层。因为笔者后文对罗氏的阶层分布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此处就不深入探讨了。
3.一般的劳动人民
在西域罗氏的职业状况中,除了以上所说的从事商贸者和任职官场者以外,更多的是一般的劳动人民。例如P.3559+P.2657+P.3018+P.2803 V《唐天宝年代(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中的从化乡22个罗氏人物应该多为一般劳动人民无疑;又如沦为下层劳动力的“作人”,据朱雷先生指出,高昌“作人”是一种与南朝“十夫客”相似的劳动人手‘136],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的作人“罗伏解”可谓是下层民众。
(二)社会阶层
在上文笔者分析了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的职业状况,那么他们的社会阶层又是如何呢?从传世史乘和出土文献中可以知道西域罗氏在中国有供职俗界的,同时也存在于僧界任职的,下面笔者就根据有关文献进行详细论述。
1.俗界任职的西域罗氏
A.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中的中上层人物,官僚阶层
在所见的有关西域罗氏或疑为西域罗氏的材料中,有一些是西域诸国中的上层人物、官僚阶层,这类材料多见于传世文献中。
这些历史人物有本为西羌种的章求拔国(章揭拔)的王“罗利多菩伽固悉立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有护蜜国的王“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莫贺达摩萨乐”,这一罗氏为吐火罗势力圈的西域罗氏,在有关材料中还见到护蜜罗氏中的“罗真檀”(《新唐书》卷22一下,《册府元龟》卷975,《册府元龟》卷964,《全唐文》卷287);另外还有一些材料提到了护蜜国王使大首领“罗友文”(《册府元龟》卷971,《册府元龟》卷976,);还有骨咄国王“罗全节”(《册府元龟》卷971,《册府元龟》卷965,《全唐文》卷39);有解苏国“罗顿毅”(《册府元龟》卷975);另有吐火罗国“罗底囗”(《册府元龟》卷971,《册府元龟》卷975);还应该提到在唐朝任职的“罗邵权”一族,其中“罗邵权”为番相(《旧唐书》卷188)。
另外在出土文献中也见到少量有可能是西域罗氏的历史人物,位列官僚阶层当中。
如大唐陪戎副尉“罗府君(甑生)”,及其祖“罗日光”(《唐代墓志汇编》第662—663页,《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274—275页);还有大唐翊卫大督“罗端罗文静”及其父隋并州太原县令“罗穆”(《唐代墓志汇编》第410页,《全唐文补遗》笫二辑,第194—195页);另外还有身处官僚阶层中的石崇俊夫人“罗氏”(《唐代墓志汇编》第1893页)。
在上述是或有可能是西域罗氏的历史人物中,大多数来源于吐火罗势力圈,如罗底囗、罗真檀、罗旅伊陀骨咄禄多毗勒贺达摩萨尔、罗友文、罗全节、罗顿毅等。其来自何国,相关材料中有明确记载,兹不赘述;另外一些西域罗氏,由于材料所限,不能明确其具体源流;由此可见吐火罗势力圈与唐朝交往密切,吐火罗势力圈内罗氏流寓中国的历史人物应该有一定的规模。
在上述列举中,涉及到西域罗氏的多是一些西域诸国与唐王朝贡使关系的材料,反映了唐朝与周边国家特别是西域诸国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其中西域罗氏在里面起了显著的作用。上述材料所见西域罗氏多为西域诸国的王、首领,确实应该属于西域上层人物、官僚阶层。
在上述列举中也有疑为西域罗氏在唐任职的,如罗邵权、罗甑生、罗文静等。这说明西域罗氏流寓中国者有进入官僚阶层的,间接证明了西域罗氏流寓中国不应该是孤立的,既然有涌人中上层者,是否可以推想还有沦为下层民众的呢?
B.西域罗氏中的下层民众
在前文笔者提到了不少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及其后裔,这里面不仅有中上层人士,还有下层民众,这样的材料多见于敦煌吐鲁番西域出土文献。
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的作人“罗伏解”可谓是下层民众,作人是一种劳动人手。另外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了贾胡商贸活动,其中含有吐火罗后裔的叙述,实为中外关系史罕见材料,据材料分析,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应为下层民众无疑。
另外,十分珍贵的敦煌文献P.3559+P.2657+P.3018+P.2803V《唐天宝年代(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中的从化乡22个罗氏人物应多为下层民众无疑,如下中户罗伏帝延、罗敬宗,下下户罗阿铛、罗仙其、罗宁宁芬、罗奉鸾、罗乌湿、罗达数番、罗双流、罗双利、罗特勤、罗顺陁、罗宾宾,另外有三个罗氏人物(罗拂那、罗湿数延、罗数延)可能因为不堪忍受赋役等原因成了逃户。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是下层官兵,如土镇兵罗铛娑,武骑尉罗阿铛等。无论是下层官吏,还是一般平民,把他们归人下层民众应该是可以的。另外,在敦煌社邑文书中也保留了一些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沦为下层民众的材料。
2.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存在任职僧界者
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在僧俗两界都有,前文笔者论述了罗氏在俗界任职的情况,材料较多;但西域罗氏在僧界任职者材料较少,今举两件敦煌卷子为例。
例一:
P.3073《庚寅年正月三日社司转帖》中的“罗僧正”,录文如下:
社司转帖
(前略)太子 翟僧正 曹僧正 安僧正 罗僧正 宋法律 戒随阇梨 王僧正 汜法律
马法律 王法律 杨法律 徐法律 阎押牙(衙) 吴押牙(衙) 阴押牙(衙) 马
押牙(衙) 高押牙(衙) 索草场 宋押牙(衙) 丑囗 阴押(衙)[137]
例二:
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前略)于阗罗阇梨身故助葬细供十分,胡[饼]五十杖,用麦四斗四升,油八合(后略)”[138]中的“罗阇梨”。
根据前文分析,这两个罗氏人物有可能是西域罗氏后裔。僧正,也作僧政,僧官名,初见于《高僧传?僧口传》;阇梨,指佛教中的高僧。很明显,罗僧正和罗阁梨都是佛教教团中的人物,在僧界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这两件涉及罗氏在僧界任职的文书中,S.1366《年代不明(980 -982)归义军衙内麦油破用历》尚在罗阁梨前面有“于阗”二字,据此,我把这一罗氏定为“于阗罗氏”,但是罗阁梨是西域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寓于阒后又到敦煌的,还是于阗固有居民(于阗居民多以尉迟氏著称,但这也不表示没有其他姓氏的存在)流寓敦煌的呢?除了这点微弱的史学信息,从两个孤零零的罗氏名字中,很难再发现其他更有价值的信息。尽管如此,从上述两件文书中,毕竟还是可以知道在敦煌文书中存在流寓中国特别是敦煌的西域罗氏的。
以上表明流寓中国特别是敦煌的西域罗氏可能存在于僧界任职者。那么,从社会阶层上分析,西域罗氏在中国涉及的层面就更广了,既有俗界的中上层官僚、下层民众,还有佛教教团人士。
(三)婚姻关系
上面我们了解了隋唐五代存现中国的西域罗氏的职业分布和社会阶层,下面再看一下他们的婚姻关系。
《大唐故石府君墓志铭并序》139记载了昭武九姓胡人后裔石崇俊的生平事迹,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出土文献。我们要关注的是石崇俊夫人罗氏,据前文考证,怀疑罗氏是西域胡人后裔。这样可以看出石罗联姻应为胡人内部婚姻。另外还有一例,那就是罗盈达及其夫人曹氏(曹议金的妹妹),在上面的分析中,笔者认为罗盈达一族有可能是西域罗氏后裔,根据学者的推论,曹议金一族已经被确定为昭武九姓胡人后裔,所以罗曹联姻也应是胡人内部婚姻。
由上可知,胡人内部联姻存现于西域罗氏后裔中;但是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也只能是这些了。
二、多元化的西域罗氏源流试析
前文,笔者列举并分析了隋唐五代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初步从罗氏人物中辨清了西域罗氏;下面笔者想对西域罗氏的源流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求搞清他们来源于哪个国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学养有限和资料匮乏,只能勉力为之,不尽妥当和片面之处再所难免。根据对以上隋唐五代西域氏资料的排比梳理,我认为西域罗氏的源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势力圈说
吐火罗国以国为姓,因而其居民多以“吐火罗”、“罗”为姓。以“吐火罗”为姓者,如阿斯塔那二九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有吐火罗后裔(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的情况,坦率地说,这类文献极少,但是确实反映了吐火罗居民的一种取姓状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以“罗”为姓,这种情况较前种普遍一些,多见于传世史乘中,正史、《册府元龟》及《全唐文》中的资料显示了这种情况,这些罗氏人物共计有:吐火罗国大首领罗底口、护蜜国王罗真檀、护蜜国王罗施伊具骨咄禄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护蜜国大首领罗友文、骨咄国王罗全节、解苏国大首领罗顿毅。上述西域诸国皆有以“罗”为姓的情况,如果把吐火罗国的罗氏解释为“以国为姓”,同时护蜜、骨咄、解苏诸国也存在罗氏,那么这些西域国家与吐火罗国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池田温氏以“吐火罗势力圈”以概之,那么我就把这种西域罗氏源流叫做源出吐火罗势力圈。从以上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吐火罗势力圈的罗氏都是吐火罗等国家的“王”,可见罗氏人物在这些国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粟特系统说
池田温先生把敦煌从化乡的罗氏也一并认作吐火罗势力圈的罗氏,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差科簿中罗氏就是源出吐火罗势力圈的有力证据,怎么就可以盲目认定他们的族源呢?有趣的是,我们却看到罗氏在从化乡为第五大姓,仅次于康、安、石、曹诸姓,约占从化乡总人数的一成,从化乡的罗氏和昭武九姓胡人后裔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同时笔者还发现在其他敦煌吐鲁番文献里面,西域罗氏和粟特后裔在一起的情况比较多,如S.2894《壬申年(972)十二月廿日社司转帖》、P.3391《丁酉年正月社司转帖(稿)》、S.1898《归义军时期兵士装备簿》、P.3458《辛丑年(941 7)押衙罗贤信贷绢契》、阿斯塔那二九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阿斯塔那五零九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阿斯塔那五一二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都督府史康柱欢等残牒》等,其中P. 3070《乾宁三年?(8967)行人转帖》更为明显,它记载了行人姓氏“龙藏破罗安张王赵阴薛唐邓令孤正等,安康石必罗白米史曹何,户户户,后齐程社桥屈韩吴高谈汜范禁龙高通”,如前所述,在被确定为胡姓的“安康石必罗白米史曹何”中,胡姓罗氏和昭武九姓胡揉合在一起让我们比较容易认为,此胡姓罗氏和粟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上,笔者初步把这类胡姓罗氏疑为粟特系统;为了稳妥起见,我不能不加些注脚,上面的分析是很浅薄和草率的,只是笔者的一种蠡测,因为未曾见到胡姓罗氏源出粟特系统的直接证据;但是胡姓罗氏和粟特后裔多次在文献中显现出来的密切关系,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三)印度说
在西域罗氏的源流中,还有一类是来源于印度的。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罗姓者有印度人罗好心。另外,《新唐书》卷221上记载的章求拔国(章揭拔)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应为印度罗氏,因为从地理方位来看,章求拔国(章揭拔)与东天竺接,应该是中天竺国的属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罗利多菩伽因悉立国是翻译的叫法,一些人名索引书籍就是把他认作罗姓,所以笔者也按此分类,这类罗姓和中原罗姓的取姓本质迥乎不同。
(四)于阗说
于阗居民多以尉迟氏称之,很少见到“于阗罗氏”的说法,笔者也仅仅在隋唐五代文献中见到两例。P.2629《年代不明(964年?)归义军衙内酒破历》中的“于阗罗尚书”和S.1366《年代不明(980 -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中的“于阗罗阇梨”,但文书中显示的胡姓罗氏是出身于阗的呢,还是其他国家罗氏流寓于阗又到敦煌的呢?由于资料所限,这些不得而知,暂时把他们称为“于阗罗氏”,权作一说。
综上,笔者把西域罗氏的源流归类总结为四种:吐火罗势力圈说、粟特系统说、印度说、于阗说。由于笔者的学养有限和材料缺乏,上述几种说法并不尽然全面、正确,分析的也不够深入和透彻,只是把它们列举出来,聊备一说;对西域罗氏源流的探析还要继续,这需要不断深挖已有文献和希冀新材料的出现,但是无论如何,笔者确信西域罗氏的源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结 论
综上论述,可以推断隋唐五代存在流寓中国的西域罗氏及其后裔,尽管有的罗氏人物只是可能为外来裔民;另外笔者把所见西域罗氏的源流蠡测为多元化的西域罗氏。对于西域罗氏的研究应该继续深入,探讨外来裔民的问题,单单依靠传世文献无疑是欠缺的,仅仅凭借姓名来推断种族当然是不够的;它的解决需要新观念的注入、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性、边缘化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二),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初版,第406页。
[2]郑樵《通志略》,世界书局印行,国学整理社出版,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26页。
[3]《魏书·官氏志》。
[4]《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二。
[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6]同上,第346页。
[7]《太平寰宇记》卷一零六。
[8]《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卷二百十七罗姓部,中华书局影印本。
[9]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88页。
[1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6页.
[Il]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1一212页。
[12]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往于中国的西域人》,《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1926年;后收入作者《东洋文明史论丛》,弘文堂1934年版,第339—410页。
[13]石田干之助《天宝十载丁籍所见敦煌地区的西域系统居民》,《加藤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1941年,第83—91页。
[14]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辛德勇译文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辛德勇译文又载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原文载《欧亚文化研究》,I,北海道大学,1965年。
[1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6—77页。
[1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0—191页。
[17]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0—432页。
[18]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59—373页。
[19]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94、396、397、398页。陆庆夫、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405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0页。
[2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载荣新江《中占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4页。原载《国学研究》第6卷,1990年。
[21]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九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22]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薄口马行时沽)考》,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00—518页。
[23]陆庆夫《唐代丝绸路上的昭武九姓》,载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4]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4页。
[25]羽田亨<“兴胡”名义考>,<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同朋舍出版部,1957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4 ~188页。
[26]尚衍斌<唐代“兴胡”与元代“斡脱”名义考辨>,<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39—44页。
[27]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1页。
[2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四),第264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九册,第27页。
[29]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9页。
[30]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39员。蒲立本《内蒙古的粟特聚落》,《通报》第41卷,1952年,第333页。
[31]《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四),第281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九册,第68页。
[32]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32 N 65页。
[33]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七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26—127页。
[34]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28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90页。
[3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6l页。
[36]“康义罗施”文书中原作“康尾义罗施”
[37]据第(四)段可知“拂延”前脱“吐火罗”三字。
[38]据第(四)段可知“色多”前脱“吐火罗磨”四字。
[39]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页、349—350页。《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七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8—89,第92—94页。
[4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39—40页。
[4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50 N198页。
[42]<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43]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第3—67页。
[4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08—268页。
[45]池田温 《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把罗氏统计为23人,有误,应为22人。
[46]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第3 N 67页。
[4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2页。
[48]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38—42页。
[49]同上。
[50]亨宁《粟特语丛考》(W.B Henning,S.ogdica),伦敦,1940年版,第6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0页。
[51]韦伯《粟特人名考》,《印度日耳曼研究》(Weber,Zur S.ogdiS. chen P.erS.onen - namegebung,IndogermaruS. che Fors. chungun)第77卷,第2—3期,1972年,第199—201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0—41页。
[52]韦伯上引文第98页。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粟特法律文书》,莫斯科,1962年,第53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1页。
[53]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92页。
[5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2—293页。原载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
[55]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64页。
[5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271页。
[5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281页。
[5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11页。
[59]同上,第411页,注(一)。
[60]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9页。
[61]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32页。又见于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2—263页。
[62]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5员。
[63]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91页。
[64]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262—263页。
[65]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93—394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0页。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70—271页,原载《历史研究》,2001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81—82页。
[6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29页。
[67]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96页。
[6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298页。
[69]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98页。
[70]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20页。
[71]同上,第319页。
[72]同上,第299页。
[73]同上,第298页。
[74]同上,第296页。
[75]同上,第327页。
[76]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四),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505页。
[77]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78]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409—417页。
[79]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1—362页。
[80]沙知编《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杜,1998年,第203—204页。
[8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85—489员。
[82]同上,第490一495页。
[83]同上,第337—342页。
[84]郑炳林先生持此说,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41—342页。另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对甘州回鹘的战争。
[85]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86页。
[86]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8—274页,原载于《历史研究》,2001第1期。
[87]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114页。
[88]同上,第99_101页。
[89]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38页,注(2)。
[90]参考陈海涛《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人华粟特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95—200页。
[91]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258—274页,原载《历史研究》2001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86页。
[92]《旧唐书》卷一八一。《新唐书》卷二一零。《旧五代史》卷一四。《新五代史》卷三十九。
[93]《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耆旧记》。
[94]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74_275页。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2—663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14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第46页。毛汉光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9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891页。
[95]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文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4页。原载《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
[96]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
[97]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58—274页,原载《历史研究》2001第1期。冯培红《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3_86页。史苇湘《世族与石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1—164页。
[9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135页。参考陈海涛《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人华粟特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95—200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2—364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2—23页。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谦读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人》,《考古》1986年第9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人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99]刘铭恕《洛阳出土的西域人墓志》,第211页。
[100]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4页。原载《国学研究》第6卷,1999年。
[101]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410页。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94一195页。
[102]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二),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初版,第406页。
[103]渚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4]此处“门”字疑为“祖”字,此后“,”省略。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也按此录文。
[10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893页。
[10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1页
[107]韦伯<粟特人名考》,《印度日耳曼研究》( Weber,Zur S.ogdiS. chen P.erS onen - namegebunS;,IndogennaniS. che ForS. chungun)第77卷第2—3期,1972年,第98、199—201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0—41页。里夫什茨《穆格山出土粟特法律文书》,莫斯科:1962年版,第53页。转引自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41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2—293页;原载荣新江《袄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
[108]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文载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135页。参考陈海涛《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人华粟特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95—200页。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362—364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2—23页。卢兆荫《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读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人》,《考古》1986年第9期。程越《从石刻史料看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109]《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中华书局,1960年。
[110]《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12]《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113]《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14]《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
[115]《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16]《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17]《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18]《全唐文》卷二八七。
[119]《册府元龟》卷九六四。
[120]《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21]《册府元龟》卷九七六。
[122]《册府元龟》卷九七一。
[123]《册府元龟》卷九六五。
[124]《全唐文》卷三十九。
[125]《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126]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辛德勇译文载《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3 N 67页。辛德勇译文又载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原文载《欧亚文化研究》,I,北海道大学,1965年。
[127]《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
[128]《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
[129]《册府元龟》称之为“罗施伊具骨咄禄多比勒莫贺咄达靡萨尔”。
[130]此处的“罗护真檀”即“罗真檀”。
[131]《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全唐文》卷二八七。
[132]《旧唐书》卷一八八。
[13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85页。
[13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32页。又见于宁可、郝春文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262—263页。
[135]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36]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2—65页。
[137]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第327页。
[13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第281页。
[139]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893页。
|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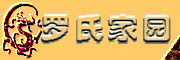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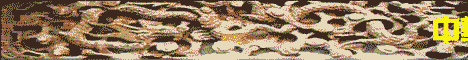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家传
罗氏家传
 罗氏家书
罗氏家书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