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士大夫评议“罗五节”忠节观的演变﹡
作者:刘正刚:钱源初
作者机构:暨南大学古籍所,广东广州510632
出版物刊名:学术研究
页码:127-136页
年卷期:2017年第10期
主题词:士大夫 罗郭佐 节义观 罗侯王庙
摘要:宋元鼎革之际,罗郭佐父子兄弟五人因事元而阵亡,被明代士人称为“罗五节”。明代以来,士大夫对罗门事元“节义”讨论持续不断,明代受“华夷之别”观的影响,评议褒贬纠结:清代在“华夷一家”观的指导下对之基本肯定,显示了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变化。清代随着民间对海洋开发的推进,罗郭佐又被形塑为保护海洋安全的罗侯王,成为民间社会的主要保护神。
宋明以来,理学家竭力强调臣民对王朝国家要尽忠尽节,尤其是在王朝鼎革之际,臣民更应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否则就会成为后世士大夫笔下的贰臣、罪人。如果涉及到汉族臣民为“夷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效力,就更成为后世仕宦们非议的对象。“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难题,也是史家文人臧否古人的争论焦点。……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问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1]实际上,在蒙古族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南宋臣民侍奉新朝者大有人在。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在宋元之际投靠元朝的石城罗郭佐及其子孙,由此引起了明清士大夫对罗家一门五节尽忠元朝的不同评判,其背后隐含的正是历代“华夷观”下的国家认同观念之变化。
一、“罗五节”事迹及生活时代辨析
罗郭佐自祖先落籍岭南后,历代仕宋,到罗郭佐时宋元鼎革,罗家一门五人转身服务于元朝,最后均战死疆场,史称“罗五节”。目前所见最早记载罗郭佐及其子孙的文献为明天顺五年李贤领衔编纂的(明一统志),引述如下:
元,罗郭佐,石城人,平海寇,以功授廉州路总管。子震,敦,化州路总管。次
子奇,雷州路同知。奇子玄珪,孙仕显,袭武德将军,廉州路同知,一门父子兄弟皆
相继死节。[2]
从这一记载可知,元代石城罗郭佐与其子罗震、罗奇,孙罗玄珪,曾孙罗仕显,一门五人均为元代地方官,为元朝尽忠尽节。这里虽没有明确说出“罗五节”字样,但实际是“罗五节”故事的雏形。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杜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09JZD0015)和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13&ZD0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正刚,暨南太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源初,暨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2)。
《明一统志》关于罗郭佐及其子孙的记载,应来源于地方文献。就是说,在此之前,岭南已有罗郭佐及其子孙的相关记载。但这些文献今日已难寻觅。罗家生活的石城县在元代与石龙、吴川三县均属化州路管辖,隶属湖广行省,明初化州改为府,属广东。[3]这里的化州、廉州、雷州等毗邻南海,位于今北部湾北部。故“罗五节”多与“平海寇”有关。嘉靖八年,江西籍人王萱撰《历代忠义录》,也简略记载了罗家尽忠元朝的事迹,“元,罗郭佐,石城人,廉州路总管。子震,次子奇,奇子玄珪,一门父子兄弟皆相继死节。”[4]王萱的记载是否源于《明一统志》,不得而知,但至少反映出罗家忠节故事在明中叶以前已受到士大夫关注。但王萱省略了罗仕显,实际只有罗门四节。上述两部史书对罗家父子“相继死节”,没有详细描述,只是笼统说他们为元朝人。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璟纂《广东通志初稿》卷13《宦绩下·高州府》继承丁王萱罗门四节的说法,但却将罗郭佐记述在“宋季”:
罗国佐,石城人,其先世居汴。祖廷玉以文学仕宋,授武翼郎、石城薄,因家
焉。子嗣宗授承信郎、石城知县。宋季,郭佐策从原征南将军史八万讨平海北,以
功授朝列大夫,寻授广州路总管,督运广东粮给饷海北军士,沿海遇贼而没。长子
震,郭武校尉、化州路管军把总,同事殁干难。次子奇,袭化州路判官,寻授奉政
大夫、雷州路同知,奉檄讨瑶寇,战而殁。奇子玄珪,亦死于难。经曰以死勤事,
诸罗有焉。
戴璟追溯了石城罗家的来源,确立了罗郭佐生活在宋季,不仅缺失了罗仕显,而且模糊了罗郭佐的信息,对“郭佐”写法不一,且将之前罗郭佐任职“廉州路总管”改为“广州路总管”。最关键的是,戴璟对谁敕封罗郭佐军功,处理得相当模糊,从字面看,罗国佐被授官职在“宋季”,实际上广州路总管设于元朝。戴璟似乎有意回避罗家事元的事实。戴璟通志中的“郭佐策从原征南将军史八万讨平海北”的“原”字,似乎暗示罗郭佐及史八万均为宋将。查《宋史》和《元史》并没有“征南将军”一职,也无史八万之人。但在元灭宋时,有元将史格“征南”,为五万户统帅,“众军渡江,平章阿术将二十五万户居前,每五万户择一人为帅统之,(史)格居其一。”[5]时南宋小朝廷巳进到南海海域,一度驻守硇洲,“元史格袭雷州”,宋高州知州李象祖叛降于元。[6]又因史格在兄弟中排行第八,故“史八万”可能是史格的别称。罗郭佐跟随他讨平海北即雷卅,很可能因此而被元封为总管。而“原”字则显示了戴璟的故意曲笔。
戴璟强调罗郭佐在“宋季”立功,这一时间概念可理解为宋元之际,即罗郭佐应为南宋降元之人。因此之故,他的子孙入元后均为官一方。元朝行省下辖地方行政建置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路之名称,源自两宋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使等,但两宋的路仅为各司其职,分立并存的监司,并未形成正规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7]即路总管应设于元代。广州路隶属于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总管府:廉州路隶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至元十七年(1280年)才设总管府。[8]因此,即便罗郭佐真的任广州路总管,也应在至元十五年后,且由元朝授予。罗郭佐长子罗震任化州路管军把总,查《元史》,“管军把总”应为“管军总把”一职,总把是介于千户与百户之间的军官,设于元世祖。[9]这说明罗震也在至元年间阵亡,且可能死于宋元鼎革之际的北部湾海战。因此,可从罗郭佐父子的任职及阵亡推测,他们为宋末元初人。
罗郭佐次子罗奇任元朝化州路判官,教授五品奉政大夫,后又任雷州路同知,在任奉檄讨瑶寇,与儿子罗玄珪一同战死。雷化二州在宋元屡生瑶乱,元人李存(1281-1354年)描述雷州瑶乱说:“窃闻黎徭民,扇据雷与廉。牧守或散走,偷生向闾阎。”[10]万历《雷州府志》卷8(建置志)记录元天历二年(1329年)“广西瑶贼侵掠”,元统元年(1333年)“广西瑶贼复陷遂溪,路总管、同知罗奉救,裨将李百户遇害”。这里的“同知罗”即为罗奇,“奉敕”与“奉檄讨瑶”吻合。罗奇父子可能在元统元年的雷州瑶乱中阵亡。
明初李贤提及的罗门五节最后一位罗仕显,一直到明末才出现较详细传记,即崇祯十年刻本《廉州府志》卷9《名宦志·死节传》,引述如下:
元,罗仕显,高州府石城人,其先世居汴,有罗廷玉者以文学仕宋,授武翼郎,
石城薄,因家焉。仕显以世功袭武德将军,授廉州路同知。元至正九年(1349年)二
月,海寇以百余艘犯合浦,帅府移檄廉琼高化以兵讨之。仕显会诸郡兵七百余,船数
十艘,追及于澄迈之石躩港。时寇沮新水,穷蹙甚,按兵严守,可计日就擒。总兵
者不知应变,督战急,屡谏不听,义士张友明等遂出战,俄而海南兵赴水走不可止。
赋乘胜四合,诸军官皆走,惟仕显及化州通判游弘道、石龙薄木蘖飞、张发明力战
而死。仕显年三十九,邦人恸之。高州志。
该传记后注明资料出自“高州志”,但现存万历四十一年《高州府志》并无罗仕显传。而罗仕显传记前半部的家族源流与罗郭佐传略似,说明罗仕显与罗郭佐有血缘关系。崇祯版《廉州府志》有关罗仕显的传记资料,可能来自于元人冯翼翁撰《元州判游公祠记》,该记在康熙《化州志》卷12《艺文二》有收录,节引如下:
化州路判官游弘道既肖先贤像于郡学两庑而祀之。至正九年春三月,侯追讨寇,
死王事,遣爱在邦,父老肖其像以次先贤,且请刻石以记。侯,临川人……初至(化
州),择要地,立营栅,以备西寇,民赖以安。……至正八年十有一月,会兵海上讨
寇,寇乘风走交趾。明年二月,自交趾掠百余艘犯合浦、琼山,帅府复命候会高化琼
廉郡兵追讨。竭己资二万缗,悬赏格从义士张友朋等七百人,船数十艘……其属石龙
主薄木蘖飞、廉州同知罗武德及张发明等皆力战以死……民不侍劝,而竟以立祠刻石
为请。
这篇记文记载了元至正八九年间,游公与北部湾沿岸地方官共同讨伐海寇而阵亡,地方父老为此立游公祠祭奠。据康熙(化州志)卷3《秩祀》记载,康熙初,游弘道被移入化州名宦祠,游公祠也“久废”。这说明元明两代地方官民一直祭奠包括“力战以死”的“廉州同知罗武德”在内的官宦。据上述祟祯版描述看,罗武德就是罗仕显。从冯翼翁的记文中可知,他与游弘道为江西同乡。冯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中进士,历官汉阳丞、湖广照磨、上犹尹等职。[11]元朝照磨“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营缮料例,凡数计、文牍、薄籍之事。”[12]时化州,雷州属潮广行省辖,冯因掌管文牍、簿籍,对地方掌故较熟悉。在此之前,冯至少为雷州、化州撰写过三篇碑记:天历年阃雷州察院记、[13]至正七年雷州儒学记、[14]至正年间化州《儒学复田记》。最后一篇提及至正六年(1346年)游弘道解决化州池氏侵占学田之事。[15]可见,冯对游早有耳闻。冯关于这场海战的描述比较形象生动,使罗仕显事迹得到彰显,并为后来士大夫书写提供了素材。我们将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的罗仕显事迹后半部分文字,与冯氏撰游公橱记内容比对,两者内容几乎大同小异。祟祯版对“年三十九”而逝的罗仕显用了“邦人恸之”来形容其得民心的形象。可见在宋亡70年后,士人或地方民众对元朝统治已产生了认同。
罗仕显在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阵亡时39岁。这一时间节点为我们辨析罗五节生活时代提供了关键信息。从罗仕显39岁可上溯他生于1310年前后,此时元朝已统治中国30多年。从罗郭佐至罗仕显为四代人,若以20至25年为一代人间隔,则四代间隔应在60至75年左右,据此推测罗郭佐约生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或淳祐十一年(1251年)前后,年)前后,宋亡时正值青壮年(28岁至43岁);罗震和罗奇则约生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或咸淳七年(1271年)前后;罗玄珪生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前后。据前面分析可知,罗郭佐、罗奇父子在至元年间阵亡。时罗震已任职,说明他是成人。罗奇、罗玄珪父子在元统元年阵亡,时罗奇约60岁左右,罗玄珪约40岁左右,时罗仕显16岁。可见罗郭佐及其子出生在南宋,在宋元鼎革之际,罗郭佐父子选择了与元合作,为元代服务。
二、明代对“罗五节”评判的分歧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王朝,其反元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已彰显华夷之别。朱元璋曾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16]然而,罗郭佐作为宋代臣民事元,其子孙也在元朝平贼中阵亡。从华夷之别的传统看,如何评价罗门五节,就成为明代士大夫的心头之痛,发声也有所不同。嘉靖时戴璟在私人著述的《新编博物策会》中即肯定罗五节的行为,与他代表官修《广东通志初稿》的含糊其辞有较大差别:
高州府:……汉谓之高凉,吴谓之高兴也。生是地者,戌日为腊,高栏为居。然
被李让之化,衣冠相尚者多也,岂复文身断发之俗乎?请具陈之:冯盎在隋击五州之
僚而拜汉阳守,在唐平诸洞之寇而封越国公。宋之时,鞠杲排章惇而甘心隶乎党藉,
虽辱亦荣矣。粱楚战交趾而备身戮于锋刀,虽死亦生矣。绍兴之间,陈焘有送母葬之
孝而两目之瞽顿明矣。方元之时,罗郭佐有平海寇之功,而一门之死尤难矣。[17]
这段史料讲述了隋唐宋元有功之臣稳定南方的事迹,已表明其对元代正统的认同,戴璟将罗郭佐一门之死,与历史上高州地区的功臣相提并论,并明确将罗郭佐置于元朝,评价罗氏平海寇有功,“一门之死尤难”。也就是说,无论是宋季还是元代,罗氏一门皆对王朝有功。
上述戴璟评论的鞠杲、粱楚、陈焘、罗郭佐四人均被列入高州府乡贤祠。罗门五节则全部列入明代石城县乡贤祠。万历《高州府志》卷2《祀典》记载如下:
高州府:乡贤祠,宋博白令粱楚,孝子陈焘,进士鞠杲,总管罗郭佐,国朝都给
事中李学曾,司务冯名望。
石城县:乡贤祠,元广州总管罗国佐,把总罗震,判官罗奇、罗玄珪,司知罗仕
显,国朝郎中李泽。
这一记载显示,明代高州府乡贤祠仅列罗郭佐一人,而石城县先贤祠则几乎成为罗家专祠。乡贤祠、名宦祠是明代在学宫内附设的祭祀有功于地方的乡邦人物,由国家、地方、民间三者合力共建。[18]罗郭佐被府县两级乡贤祠祭奠,且“罗五节”被全部放置于百城乡贤祠。罗仕显还以“元廉州路同知”身份人选廉州府名宦祠:[19]据此可以确认,明代高州士人几乎都把“罗五节”作为正面形象加以祭奠。
明中叶以后,南海士人郭棐,曾师事湛若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纂修多部地方志,主张地方志耍秉笔直书。他在万历二十三年成书的私人著述《粤大记·自序》中标榜历史书写需要公正:
昔贤云: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也;志者,郡国是非之权衡也。其所是者,必天
下之公是,而不敢诳以为是;其所非者,必天下之公非,而不敢诬以为非。有似是而
非者,剐亦不得栀蜡而饰以为是也;有似非而是者,则亦不得罗织而诋以为非也。昔
司马迁称良史,论者犹讥其是非之颇谬于圣人。况未望迁眉睫乎!是故必公是公非,
不虚不隐,而后可无愧于月旦之评也。[20]
韩棐从“不虚不隐”的是非观出发,在《粤大记》中将罗五节列入“献征类·精忠大节”,表明罗五节是“天下之公是”的忠节人物,但时问却放在“宋季”。但实际上,郭棐在不同著述中对罗家的评价有所不同。他在纂修《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刊刻)中,对罗五节给出了另一种评判:
论曰:余观高之名贤,其砥行独修者十有七人,而死难之士十有一人。噫!夷齐
之饿,比千之剖,自昔难之。高在偏隅,而何其忠臣烈士,斌斌辈出栽!冯盎当隋之
末,控州二十,拓地千里,犹不敢自王,其忠唐大节业,亦为高郡树赤帜矣。迨宋有
鞠杲者,誓不与章惇共国,汴京一疏,千古而下,凛有生气。士生于此,稍知自好
者,有不闻风而起乎?是故蒋科,余表、梁瑶、李学曾各守其官。而李泽、黎盘弗善
事权宦,斯亦持正不阿者矣。身遭炮炙,不塞骂贼之口,如粱楚死有余光。张友明、
张恒、张韬、潘斗辅,后先合辙。阵思贤辈坚不迎靖难之书,则尤其皎皎者也。姚岳
祥恶奸臣卖国,初授美官,旋归田里,可不谓见几而作乎?独罗郭佐五人历世事元,
尚论者虽不能无遗憾,然食君之禄,能死君之事矣,亦可以为偷生泄泄者戒也,姑并
存之。[21]
很显然,这部代表官方态度的地方志,对罗家“历世事元”,难以释怀。作者认为“夷齐之饿,比干之剖”的忠义观在高州已深入人心,引起历代高州忠臣烈士“斌斌辈出”。对罗门五人以“独”字突出了其不满,又以“食君之禄,能死君之事”,作为“偷生泄泄者戒”而存之。他在《广东通志》卷52中时《粤大记》卷15《献征类·精忠大节》略作修改,收录了罗门五人,内容相差无几,都将罗郭佐放在“宋”目下,并首用“罗五节”的说法:
罗郭佐,石城人,先世居汴。祖廷玉以文学仕宋,授石城薄,因家焉。宋季,郭
佐平海寇有功,授朝列大夫、化州路总管,寻授广州路总管,督运广东粮饷给海北军
士,海上遇警骂赋而死。长子震,郭武校尉、化州路把总,同事殁于难。次子奇,袭
化州路判官,寻授奉政大夫、雷州路同知,奉檄讨瑶寇,挺身杀赋,为贼所害。奇子
玄珪救父死之。孙仕显袭武德将军、廉州路同知,至正间督战船,会高州琼廉等郡官
兵剿海寇,战殁于石躩港,年三十九。一门父子昆弟子孙五人相继死节,粤人称为罗
五节云。
郭棐在前之评述中说罗五节“历世事元”,这里又将罗郭佐说成是“宋季”,表明其摇摆不定的态度。郭棐以中原正统自居,对元朝充满“敌意”,可从他在万历《广东通志》卷19《郡县志六》对涉元的评述可见一斑,如评“达鲁花赤”说:“元以胡虏入主中国,恶华人非其类,乃于诸路总管之上各置达鲁花赤黔制之,郡邑皆然。达鲁花赤者,华言囊口压子也。今存其官而削其人,见胡虏能抑吾类于一时,不能逞威焰于异世云。”又评“宣慰廉访”云:“按旧志胡人仕宣慰廉访者悉录之,连篇累牍,令人邑邑不平。兹惟录其有声者,余并黜削,云不与元也,亦春秋外夷之意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赞扬“罗五节”的节义行为,但又不承认元朝的地位,只好将罗家模糊地放置在宋季。
郭棐尽管代表两广总督修《广东通志》,但他对罗家的评判并没有为当时人接受。万历年间,高州知府曹志遇纂修《高州府志》卷6《节义》则将罗郭佐及其子孙放在“元”下,并借用郭通志的“罗五节”说法,文字表述几乎一样,仅将郭通志中的“宋季”改为“元初”。查雍正《广东通志》卷4l《名宦志》记载,曹志遇在万历四十年出任高州知府。相信曹志可能抄袭郭志。郭志和曹志对罗郭佐生活时代的改写,可看出朝代对罗家评价的复杂性。曹府志明确罗为元人,并专门将之与晋朝卞壶父子作比较:
论曰:卞望之父子捐躯于典午之朝,江元亮弟昆毕命于太清之季,并垂青史,世
为美谈。然未有五节萃于一门,如高凉之罗氏也!自佐至显,代有其人。咸怀不二之
心,共笃在三之义。虽名未著于当年,而志无惭于往哲,讵可以位望之徽,而略其忠
贞之节也?通志以历世事元为有遗憾,嗟夫!元不得君臣乎哉?[22]
在曹志遇等编者看来,相对于卞氏父子、江氏兄弟而言,罗氏“五节萃于一门”,且“咸怀不二之心”,所以他们的志节无愧于卞、江。曹志还对郭棐通志的“历世事元有遗憾”,发出了“嗟夫!元不得君臣乎哉”。很显然,曹的府志赞成罗家为元节义。其实在宋元鼎革之际,高州也有仕宦与宋朝共存亡,戴璟《广东通志初稿》记载茂名潘惟贤父子三人在抗元斗争中的事迹,与罗家降元形成了比照:
潘惟贤,茂名人,举乡试,补本县尹。咸淳中,闻元师所向皆捷,乃诣行在,奉
命守御白沙寨。见元师日迫,人皆奔降,仰天大恸曰:“自古及今,岂有犬羊而为中
华主邪?吾为宋臣,当为宋鬼。”元师奄至,拒之弗敌,被执至电白留用之,惟贤诟
云:“臊羯狗,吾岂以衣冠而混左袵,宜速杀我”。遂遇害。长子斗辅,伏剑窥父所
在,袭而不克,死之。次子梅窗亦欲往,斗辅以无后戒,今择善地去之,以存宗祀。
时以为一死节、一赴难、一存宗祀,潘氏三贤云。[23]
潘惟贤在宋元鼎革“人皆奔降”的形势下,仍听命于在硇洲岛“行在”皇帝的指令,率军守御白沙寨,坚持“吾为宋臣,当为宋鬼”的信念,最终战败被俘。此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电白籍进士黄子平撰《潘氏三贤记》说得更为明白:“惟贤潘公,宋高州军茂名县博铺乡万平里田藔村人也。……以乡贡拜茂名县尹,九载无代。时咸淳末年,天下鼎沸,元室方兴,游兵将抵高州。宋幼主自闽渡海至那黎港……海滨父老争以牛酒迎劳,公亦以职上觐,奉命守白沙寨。[24]在潘惟贤就义前,其长子潘斗辅欲救之,结果父子同亡,次子为保存“宗祀”血脉而隐居,获得“潘氏三贤”美誉。
但这个故事并未为郭棐所接纳,他在万历《广东通志》卷52《孝友》将潘斗辅放在“国朝”条下,讲述他有“奇节。父惟贤被瑶执至寨。辅备厚金求赎,贼不受必欲杀之。辅请以身代死。贼竟杀父,斗辅怒发持剑誓驰寨歼贼。”而万历《高州府志》卷6《孝友》也以潘斗辅为主角出现,同样也放在“国朝”。但据道光《广东通志》卷298《列传三十一·高州》考证,潘斗辅应为宋代人。
上述万历《高州府志》将罗家与晋代卞望之作联想,在黄子平的《潘氏三贤记》中也出现将潘氏与卞壶相提并论,引述如下:
昔卞壶力疾战死,其子眕、盱赴贼就烹。《晋史》以忠孝萃于一门称之。微子逃
殷归周,孔子目之为仁。盖壶之力战,非伤勇也,忠臣之义也;眕、盱之就死,非轻
身也,孝子之义也。微子之出奔,非惧祸而偷生也,宗祀之寄重也。是虽有生死之不
同,而同归于一。揆者皆适乎义耳。窃观潘氏三贤,其亦庶几矣乎?惟贤不忍忘君而
事仇,斗辅痛父而忘其身,梅窗受兄之命,全躯以为潘氏宗祀,千载之图,视古人何
歉焉![25]
卞壶和卞望之为同一人,在东晋成帝咸和初发生的苏峻之乱中战死,两个儿子也“相随赴贼”而遇害。[26]江元亮则在南朝粱武帝太清年间候景之乱中,与两个弟弟皆在平乱中“毕命”。[27]卞、江因此忠烈而留名千古,成为后代忠君爱国的榜样;与潘家在鼎革之际“不忍忘君而事仇”相比,罗五节“历世事元”就显得很另类,诚如前引郭棐所云:“论者虽不能无遗憾,然食君之禄,能死君之事”,即罗氏在本质上也尽忠报主,与潘氏三贤抗元尽忠一致。可见,明代士大夫对罗门五节的评述始终处于矛盾中。
元灭宋后,元初广东士人大多不仕元,“旧朝士人不仕新朝为列代所常有,而广东士人家族在80余年长期不仕元之举,却在历史上甚为突出。”①李治安认为,“元朝是中国第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程朱理学继续发展和官学化的时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恰恰在最讲究'纲常'、'名节'的理学官学化的元代,却出现了以理学宗师许衡为代表的中原文人士大夫纷纷仕蒙,出现了南宋末较多士大夫望风降元和元末较多汉人进士以身殉国。”这与元初华夷正统观的演进有关,时中原士人演绎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正统说。[28]因此,罗郭佐选择了与多数广东士人不同方向,走上了仕元之路,似乎与当时的主流合拍。就此而言,似乎又能给予同情之理解。
①参见方志钦;《广东连史·古代上册》,厂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杜,2010年,第949页
三、清代对“罗五节”行为的肯定及其神化
明朝关于罗氏仕元的不满主要出于华夷之别的正统观。代明而起的清朝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正统士大夫眼中同样是异族统治中国。那么清代士人如何评价宋人仕元,实际上就隐含着清朝是否认同元朝大一统的问题。有学者强调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由民族认同做保障。[29]清朝和元朝同为“征服王朝”,清对元持完全认同的态度,士大夫对罗五节的评价也一致肯定。清代将罗郭佐列入忠义祠,塑造成忠义代表,并逐渐塑造成粤西地方保护神。
清前期士大夫肯定罗氏“历世事元”,康熙六年《石城县志》下编卷3《人物》记载:“叙曰:乡愿者流,以善斯为得计,乃至乡评论定之后,气焰都灰,惟有峻骨流芳,死乃不朽耳。石之乡达者希得,崇祀俎豆仅二氏焉。后之允协与论,无愧乡评者,亦得论列而附之。”编者所列石城第一个乡贤就是元代罗郭佐,“本县元时人。……宋季,郭佐策从原征南将军史八万讨平海北,以功授朝列大夫……昆季子孙咸受爵秩,相继死之。祭法曰以死勤事,罗氏有焉。”很显然,罗家是经乡评后“死乃不朽”的乡贤。编者对前朝旧志非议罗氏“历世事元”,明确表示反对。引述如下:
论曰:今夫论人亦难矣,虚声固多,术寓隐德,岂无剑埋,才与遇违,行与时异。
其中又有幸不幸焉,或望光焰于朝端,而反隐玷于乡里者有之。然到乡先生之得祀于
乡,夫岂易哉。如罗氏之贤以死勤事,于祀典诚不爽也。乃旧志以其事元为憾,要未
设身处地耳。夫以一门五节,古今所希,在元事元,庸何伤乎?……十步之内,不无
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在同教者表而出之,庶几风声一丕变耳。
编者直接指出罗氏符合《礼记·祭法》规定“以死勤事则祀之”的精神。[30]显然此处的祭祀标准体现的是个人自身的行为,并未涉及尽忠对象是否有华夷之别。罗氏为元朝尽忠受到明朝某些士大夫的非难,但清代编者旗帜鲜明予以肯定,提出旧志未设身处地思考问题,得出“在元事元,庸何伤乎”的结论,即“在元事元”值得肯定。可见,清前期和明朝对罗五节“事元”问题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看法,华夷之别在此呈消弭之势。
康熙十一年纂修的《高州府志》也强调在变势中体现的节义为“不幸”,但仍值得“嘉表”。“节义者,臣职之不幸也,曷言乎?臣职之不幸,变也。家有变而子之孝见,境有变而臣之节见,故曰不幸也。然境之不能不变也,势也。势不能不变,而无以殉其变之人,君无如臣何,天地亦无如人何。无如何则可以不尽曰非也。必如何而尽者,法也,非节也义也。不如何而尽者,性也,诚节也义也。尽性者可嘉表出之,以厉人臣之死于其职者。”。[31]编者认为时势造就的社会变化难以阻挡,对“节义”的理解也应有所变化,言谈之中,有意淡化了“节义”的对象,仅以“境”和“君”模糊指称,表达了对罗郭佐“尽性”节义的肯定。罗郭佐即收录在该志的“节义”目下。
清代广东士人讨论罗家的忠义,也引起了其他区域士人的关注。康熙三十八年浙江钱塘人进士邵远平编纂《续弘简录元史类编》,认为明初《元史》对元朝忠臣义士“所载十不得五”,遂“遍加搜集,以补旧史之失。彼既不惜一死,我敢蕲此一书。”[32]在该书卷14《旌德四》中收入罗郭佐及“罗五节”的简单传记。康熙年间,江西广昌人进士魏方泰撰《行年录》转引《广东志》收录了元朝罗仕显传。[33]这两人皆在朝廷为官,基本反映上层对罗家的肯定。
清前期对元朝的政治认同,还可从其表彰忠于元朝臣民中得到印证。元代广东吴川人刘承忠任职江淮,驱蝗有功,在元明交替时誓死捍元而投河自尽。清前期对驱蝗神刘猛将军的认定,其实有宋朝刘锐、刘锜和元朝刘承忠等原型,但王朝认同的是刘承忠,“用殉忠于蒙古王朝的汉族武将来代替刘锐及刘锜那样顽强抵抗蒙古、女真的汉族英雄,强制建庙祭祀,从中不难看出满洲王朝统治的良苦用心吧”。[34]因此之故,清前期对“事元”罗五节肯定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清代罗五节所在的地方通过建祠祭奠罗五节。雍正年间,下诏“各省立忠义祠,凡已旌表者,设位祠中,春、秋展祀”。[35]石城县于雍正三年(1725年)在教谕署前建忠义祠,祀罗国佐、罗福牌位。罗福是罗仕显之子。据康熙六年《石城县志》卷3《忠义》记载:
罗福,本县人,元时为化州路枢密院同佥,素有勇略。顺帝十五年(1355年)山
海贼麦伏、黄应宝、潘龙等聚众割据雷州路。十九年,福领兵击之,诸贼败走,以保
障功升本州岛都元帅。元末兵起,岭表骚然,福乃专制其地。及明兴,洪武元年征南
将军驰檄徇郡县,福遂以高雷归附,时改化州为化州府,领本县,隶海北道。福之知
兴识主,顺从恐后,列诸忠义,谁曰不然?[36]
罗郭佐出生南宋而投降元朝,罗福出生元朝而投降明朝,两者均能顺应时势,故得以列入忠义祠。当然,这与清前期“华夷观”变化有关,“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竣挑战。”清前期皇帝多公开标榜“天下一统,华夷一家”。[37]因此,石城忠义祠奉祀的罗氏均效忠“异族”建立的王朝。另据光绪《高州府志》卷13《经政》记载,光绪时罗郭佐又从乡贤祠被调整到高州府名宦祠中。
清前期地方官员对罗五节忠义的肯定,引发了地方不断挖掘罗氏家族资源的行动。明代文献没有记载过的罗家墓冢,清代在其家乡石城县被一一“发现”。今人编修《廉江博教、安铺罗氏族谱》声称,“原谱记载郭佐公之墓当年被别姓冒占及重葬过程”:“郭佐公之墓奉旨敕葬在名教岭,坟茔左右立有石猪石羊,故今号为石羊坟。因曹信盗此碑记,雍正三年品隆公往上司控告有案。”[38]文中“奉旨敕葬”,此前未见诸史册。其中的雍正三年罗品隆控告曹信偷盗墓碑案,则说明石羊坟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罗家后人控告曹信的时间点恰好是当地奉旨建忠义祠,这暗示罗家因应官府而开始家族扩张的动作。因为曹信拥有“太学生”功名,在地方有一定势力,曾在康熙五十年捐资帮助石城知县孙绳祖移建松明书院。[39]
罗郭佐墓被发现后,很快引起官府重视,乾隆二十四年《高州府志》卷4《地理·茔墓》记载,石城县有“广州总管罗郭佐墓”。光绪十八年《石城县志》明确记载罗郭佐墓在“邑西名教蛉,离城百五十里”,并注明是参考嘉庆二十五年《石城县志》的参访册。不仅如此,又发现了新的罗氏家族墓葬,“宋主簿罗廷玉墓在邑西纱帽岭,离城六十里”;“知县罗嗣宗墓在邑西皇岭,离城八十里”;“元雷州路同知罗奇墓在县西百二十里,土名象牯岭”。[40]可见,罗家始迁祖及后代祖墓都位于县城之西。不管这些坟墓真伪如何,都反映了当时高州地区需要罗家资源来达到某种社会效益。
随着清代仕宦认同并形塑“罗五节”正面形象的展开,罗五节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忠义的典型形象,成了地方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罗郭佐开始由人走上神坛,至少从乾隆以后开始,高州和雷州地区出现“罗侯王”信仰,光绪《吴川县志》卷3《建置·坛庙》根据采访册记载“城西南六十里麻斜讯”的罗大人庙(一称罗侯王庙),编者按语说:“高雷乡间多祀之,称曰佐国侯王罗大人。窃疑佐国二字乃郭佐之讹,实祀元化州路总管,石城罗郭佐也。”其实百姓并不关心罗大人具体名讳,他们只关心神祗对地方有功即可。所以编者在评述地方社会祭祀罗郭佐时说:“郭佐讨平海北,功被高雷,骂贼捐躯,忠义显赫,民间尸祝,于理固宜。”即罗郭佐有功于地方,理应受到民众祭祀,完成了由人到地方保护神的角色转变。从人到神的转变还需要有“显灵”故事发生。罗大人信仰也少不了这一环节。光绪《吴川县志》卷3《建置·坛庙》在“罗大人庙”条目下转引了一则故事:
《孙氏族谱》云:世传素庵祖自闽官雷时浮海来,适大雾,波涛骤起,舟行不知
所届。忽有竹附舟上,书“佐国侯王罗大人”,因随竹所指,遂抵雷。子孙世世祀之
不改。考孙梅心官雷州在宋理宗时事,前于罗郭佐,窃疑《孙氏族谐》未确也。
《孙氏族谱》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吴川唐基村孙大焜编纂。据光绪《吴川县志》卷8《流寓传》记载,孙家入雷始祖孙梅心,号素庵,福建长乐人,“宋举人,任雷州教谕,致仕,卜居于吴之唐基”。方志编者因孙梅心生活在罗郭佐之前,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实际上,民间社会对神灵记忆往往会发生时间错位或嫁接,更何况宋代距离咸丰年间已超过数百年。孙大焜是举人,曾任当地高文书院主讲。他修谱的原则是“盖族谱不患世系之不明,而患立意之未善”。[41]本着“立意”的心态,自然就难以准确考究其始祖与罗大人的关系了。但这一历史记忆恰恰又反映了罗郭佐信仰与海洋社会之关系。高、雷地区为海洋社会,与海内外交流多通过海洋进行,[42]罗郭佐及其子孙也多因平海寇而战死,其信仰带有明显的海神气息。我们之所以这样判断,还可以从布防驻扎在高雷地区的清代水师奉祀罗犬人得到验证。吴川麻斜港侯王庙现存两通石碑,一为道光二十一年《罗候王庙香灯勒示》,碑文风化剥落,难以辨认。但碑记开头有“特授吴川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纪大功二次冯……”,中间有“麻斜有罗侯庙,敬给四方官军”等字样。[43查立碑时吴川知县为冯云路,安徽人,进士,[44]道光十五年二月任吴川知县。冯知县立碑内容已不可考,然碑文的”四方官军”,应与清代地方军事存在关联。一为光绪十九年《重修侯王爷庙捐题碑记》。[45]在捐款名单中,除吴川知县李之藩外,出现丁不少军官名录,如吴川营都府陈元杰、守备李炳超、刘守府、左部总司叶向荣。陈元杰是东莞人,光绪十三年任,“俱吴川营都司,十四年改归高州镇标”;[46]李炳超是香山小榄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广海营守备升都司”,[47]光绪八年始任职吴川营;叶向荣是阳江程村人,光绪时任“本镇左营把总”。[48]还有来自霄州府遂溪县的东山营军官分府崔鄂培、周分府、陈总司、王副分府和副总司吴明昭等。
这些地方驻军如此重视侯王庙,与罗五节多在海上征战有关,希望藉此保佑海上平安。而罗侯王庙所在的麻斜港自康熙迁界以后直到清末都是重要军事据点,“康熙元年奉旨迁移,滨海居民俱归内地,钦差大人科解巡察形势,自里湿岭至麻斜一路立界墩台二十二处”,麻斜设有炮台、墩台等军事设施。[49]嘉庆年间,海盗郑一将各路海盗统一为海盗大联盟,一度以广州湾和硇洲岛为据点,屡次袭击沿海要塞,官兵屡屡受挫。吴川沿海成为水师抵抗海盗的防御线。②光绪《高州府志》卷54《纪述七·杂录》记载:“吴川,海疆一大关口也,贼舟泊广洲湾,入限门,攻麻斜”,可见麻斜在海防中的重要地位。道光《广东通志》卷298《列传三十一·高州》记载,嘉庆六年(1801年),吴川人房士升为防守麻斜汛把总,遭到海盗突袭,“汛几陷,守障者皆哭”,最终仍不敌海盗,房±升及官兵全部遇难。[50]于此可知军人祭拜罗郭佐的某种缘由。罗郭佐在海上剿平海寇,吴川又以海上防务为主,加深了官兵对罗侯王庙的情感认同,罗郭佐被地方官民纳入海神系统,目的就是求得海洋社会稳定。
罗大人信仰的起源是民间社会在先还是官兵在先,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在罗大人信仰产生后,肯定得到了官府支持,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官府对罗五节忠义行为的肯定。也正因为如此,罗五节尤其是罗大人信仰渐渐在粤西社会蔓延,罗郭佐遂成为地方社会保护神。至今每逢罗大人庙会之际,麻斜罗侯王庙在游神过程中,都要举行罗侯王的海上巡游,而罗侯王庙也被纳入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②参见[美]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刘平译,北京: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5、69页。
宋元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重心已转移到南方,海洋开发尤其是海洋贸易盛极一时。正因为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宋元在南中国海域完成政权交替的长期鏖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本文讨论的主人公罗郭佐与其子罗震就是在“督运广东粮给饷海北军士”的途中阵亡。明清时期,海洋开发依然活跃,但出于明清王朝抑制民间开发海洋,阻碍了民间海洋事业的顺利发展,[51]导致海洋盗贼之患不断。地方官府为了稳定海疆社会,积极挖掘有关保护海疆安全的文化资源,石城“罗五节”中的罗郭佐及其子罗震、玄孙罗仕显等因战死海疆,元明之交的罗福也屡屡征讨“山海赋”。也就是说,明清士大夫关注“罗五节”,与宋代以来海洋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联。
本文的研究表明,“节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52]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淀而完善,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罗郭佐作为宋代臣民,在宋元鼎革之际,毅然服务于元朝,因此而引起了明清士人对“罗五节”尤其是罗郭佐“节义”的论争。明代士大夫局限于儒家正统“华夷之别”的束缚,对“罗五节”忠于元朝难以释怀,纠结于“罗五节”的“事元”情节,或模糊罗郭佐生活时代,或刻意回避其节义的王朝对象,体现了明代受“北虏南倭”困扰下的价值取向,对在宋元交替中服务于元朝的罗郭佐心存芥蒂。但面对海疆社会的不稳定,又不得不对罗家保卫海疆而献身的精神予以肯定。明代士大夫对“罗五节”形象塑造的焦虑,到了清代,随着王朝国家对“华夷之别”观的调整,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新思维。与此同时,面对海洋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持续增加,士大夫们几乎一致认同了“罗五节”的正面形象,罗郭佐被列入忠义祠,塑造成节义的典范。官民又共同将罗郭佐送上神坛,形成了罗侯王信仰,罗郭佐渐渐成为保护海洋安全的海神,演变为粤西地方保护神。可见,传统社会的节义观随着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而逐步调整,从而成为不同族群共同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巨》,《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古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阜,笫144-157页。
[2]李贤:《明一统志》卷81《高州府》,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016页。
[3]康熙《化州志》卷1《沿革》。
[4]王蓂:《历代忠义录》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3册,济南:齐鲁书杜,2001年,第282页。
[5]《元史》卷155《列传第四十二·史天泽》,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64页。
[6][14][23]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行次》,卷16《学校·雷州府儒学》,卷15《人物》。
[7]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8]《元史》卷62《志第十四·地理五·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15页;卷63《志第十五·地理六·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第1538页。
[9]《元史)卷98《志第四十六·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8页。
[10]李存:《俟庵集》卷1《汪巡检南雄官满过安仁将北上赋诗为别》,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05册,北京:商务印出馆,2005年,第430页。
[l1]刘岳申:《申斋集》卷11《碑志》,文渊阁四库全数集部第40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5页。
[12]《元史》卷85《志第三十五·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125页。
[13]万历《雷州府志》卷20《艺文志》。
[15]乾隆《化州志》卷10《艺文下》。
[16]《明太祖实录》卷26,昊元年十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话言研究所,1962年,第407百。
[l7]戴璟:《新编博物策会》卷16《广东省·高州府人物》,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18]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完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9]乾隆《廉州府志》卷6《建置》。
[20]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点较:《粤大记》上册《自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
[21]万历《广东通志》卷52《郡县志三十九·高州府》。
[22][25]万历《高州府志》,卷6《节义》,卷9《文略》。
L24]《潘氏三贤碑》,光绪《电白县志》卷27《纪迷三·金石》。碑注云:此碑在潘惟贤墓右,题为“宋潘氏祖公遗行碑”。
[26]《晋书》卷70《列传第四十·卞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2页。
[27]《通志》卷166《忠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85页。
[28]李治安:《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29]刘凤云:《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研讨综述》,《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0]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礼记·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6页。
[31]康熙《高州府志》卷6《节义》。
[32]邵远平:〈续弘简录元史类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页。
[33]魏方泰:《行年录·三十九岁》,四库奎书存日子部第23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809页。
[34]【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4-55页。
[35]《清史稿》卷87《志六十二·礼六·吉礼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600页。
[36]康熙《石城县志》下编卷3《人物》。
[37]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斫究》2005年第4期。
[38]《廉江博教、安铺罗氏族谱》卷1《三世祖》,1992年印行,第15页。
[39]光堵《高州府志》卷14《经政二》。
[40]光绪《石城县志》卷3《建置·名墓》。
[4l][46]光堵《吴川县志》,卷9《纪述上》,卷5《职官表》。
[42]刘正刚:《唐宋以来移民开发雷州半岛探析》,《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43]2015年3月1日,笔者抄录于湛江坡头区麻斜侯王庙道光二十一年《罗侯王庙香灯勒示》碑刻。
[44]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157《选举志》。
[45]2015年3月1日,笔者抄录于湛江坡头区麻斜侯王庙光绪十九年《重修侯王爷庙捐题碑记》碑刻。
[47]光绪《香山县志》卷11《选举表》。
[48]民国《阳江志》卷28《选举志三》。
[49]康熙《吴川县志)喜3《武备志》。
[50]道光《广东通志》卷298《列传三十一·高州》。
[51]范全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比坷海洋事业的阻碍),《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5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支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相关链接: 湛江罗侯王庙会晋升省级非遗 湛江罗侯王庙会晋升省级非遗 |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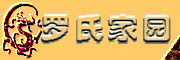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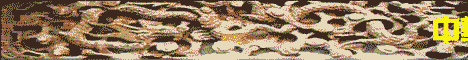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家传
罗氏家传
 罗氏家书
罗氏家书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