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琐忆父亲罗怒涛
作者:罗乔敏http://www.luos.org 在母亲晚年喋喋不休的唠叨中,有一个叨念渐次多了起来:你父亲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这大约是在夕阳残照下,登上记忆的巅峰,“回首夕阳红尽处”,在心灵深处留下的一抹光辉。它使我在父亲辞世半个世纪以后,才感到为人之子在感情上的负载与歉疚,于是,对父亲支离破碎的回忆也次第涌出。父亲有一张典型的巴蜀汉子的脸:清朗的线条、略带白净的脸色,有如简洁的山水画在惨淡的灯光之下露出凄苦的微笑。而那对剑眉,又如浓墨重彩横陈在额头,行至转角处却戛然而止。
关于父亲的情况,从湖南档案馆寄回的简历有稀疏的几笔记载:罗怒涛,字德馨,别号破浪,四川省南川县人,黄埔军校七期步兵科毕业,黄埔成都本校副官处少将副处长。这些疏疏朗朗的记录只在人生的抛物线上标明了起点和拐点。在父亲走出黄埔以后,自然少不了一番征战杀伐,而在抗日战争中,就曾随部队追南逐北,先后参加过古北口、台儿庄抗战,戍边滇东南,继而随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并驻守越南海防。回国后调成都军校任职,成都解放前夕,率部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退役回家,时母亲已先期回到老家三台,父亲退役后亦回到三台,此后,为生活打拼,餐风宿露难辞,引车卖浆难避,最后,在不公正待遇中染病不治,抛妻别子而去。生不满花甲,盛衰际遇象乱石铺街一般镶嵌在人生的道路上,荣辱交相寓,苦乐交相容。有人说:经历本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如此,父亲一生,足也。
我曾试图在父亲身上找出一些旧军官的特征,然而却不甚了然,最大的特点恐怕就是“暴跳如雷”的脾气,这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的对旧军官的畏惧与惊恐,自然的植根在父亲身上。每当他柳眉倒竖时,就让人感到在怒目中潜伏的隐隐雷声,可是他却每每会在一怒之下又紧咬牙关,而雷声却在尚未生成时渐行渐远,直至了无踪迹。而他发怒,对我而言,则常常是因为我不能在严守老师的教导上作到不折不扣。但是,谁曾想,老师的一般性要求到了他那里竟会是这样一丝不苟。
父亲的眼神虽然不乏力度,却每每使人感到“雷声大雨点小”,他很少对我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有之,在儿时的心中也只是一些“雕虫小技”。他曾津津有味的给我讲述:纪晓岚小时在一个姓石的先生手下读书,一天,因贪玩弄死了一只麻雀藏在砖后,石先生发现了,要处罚他,说,如果他能即时对上老师出的对联,可以免罚。石先生当即出了上联:“细羽麻雀砖后死”,纪晓岚随口答道:“粗毛野兽石先生”。父亲这样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才就能补过,而丝毫没有埋下跟老师对着干的潜意识。有时,他强行要教我唱歌,他唱歌,洪亮的声音裹在重浊的川东口音里,从喉咙中憋出来:“我们的祖国,又大又美丽……”。我不学,说是老师教过,于是他自顾自得意洋洋的唱他的。直到初二时,我因重病在医院昏迷了三天,醒来时,见到的是在身旁守候了三天三夜的父亲,他见我终于醒了,凑上来问了我几个诸如“想吃什么?”之类的常规性问题,然后走到窗前,默默的哼起那首歌:“我们的祖国,又大又美丽”……
随着极左路线升级,父亲也处于生存的边缘状态,不久,阖然长逝,并在"不影响子女"的愿望中尸骨无存。
五十年过去,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不妨坦然以对。
噫吁嘻,花开花落两由之!
相关链接: 黄埔成都本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 黄埔成都本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 |

 罗氏家乘
罗氏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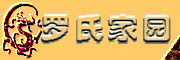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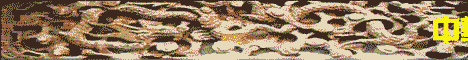
 罗氏家族
罗氏家族
 罗氏家话
罗氏家话
 罗氏家传
罗氏家传
 罗氏家书
罗氏家书
 科技天地
科技天地
 它山之石
它山之石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